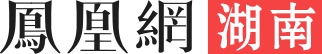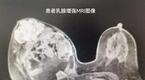湖南法治报报道!长沙公安治安民警的讲述
3月28日,倒春寒的湿气顺着窗缝往骨头里钻。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治安一大队办公室里,58岁的吴克和右手食指机械地按着左手腕关节。腕关节处向手臂延伸的深褐色疤痕像一条蜈蚣。
那是2004年雨夜,被犯罪嫌疑人用刀剐出的豁口,缝了23针的皮肉早长好了,可每逢阴雨天,就有反应。他说——
一变天,骨头里就像有蚂蚁在爬,止痛药也没用。
那是2004年5月27日留给我的特殊印记。我更愿意称它为——勋章。

我当时在西长街派出所工作,刚端起饭碗,对讲机里传来指令:“吉祥巷小饭店里有人持刀行凶!”
我马上丢下筷子,抄起警棍,带着两名队友冲了出去。
现场一片混乱。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挥舞着菜刀,在饭店里疯狂劈砍正准备冲出去。
我堵在门口,厉声喝止:“把刀放下!”但对方充耳不闻,反而挥刀朝我扑来。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冲到街上去。
那会正是饭点,巷子里挤满了吃饭的人。让他持刀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我来不及多想,身体比脑子反应快,一个箭步上前,试图抱住持刀人的腰,对方却猛地一刀朝我劈过来——左手腕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剧痛之下,我只能踉跄后退,但仍死死挡在门口。
不能让他冲出这个门!我当时心里就这一个念头,我顺手拿了条凳子准备将男子手中的菜刀打落。第二刀砍在我的左手肘上,我好像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
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我的意识已经模糊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去想,持刀的嫌疑人控制住了吗?群众没事吧?现场伤亡情况怎么样?
在医院,我的左臂被打入14根钢钉。医生告诉我:“骨头断了,肌腱也断了,这只手以后可能连握拳都难。”

我听完后只问了一句:“我还能当警察吗?”
“能。”
只要还能当警察,那就行。
我开始用心康复。康复并不是很顺利——左手臂骨头被砍断,身体多处骨折、挫伤。第一次手术接错了肌腱,拇指无法弯曲,医生不得不敲断重新缝合。
3个月后,我把伤残证明锁进抽屉,揣着七级伤残鉴定书回所里报到。

妻子把熨好的警服拍在我胸口嗔怪道:“下次挡刀前,想想儿子画的全家福还在床头挂着。”我摸着左臂凸起的疤痕没说话——那些无辜的群众,谁家床头没张全家福?
我不敢开口,对家庭,我有些愧疚。
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组织上照顾我,想调我去轻松点的岗位。
“干公安工作哪有什么轻松的岗位,我能坚持的。”我跟分管领导坚持。
我还是回到了西长街,我熟悉的地方。

那时,西长街有劳务市场、药材市场、水果市场、海鲜市场、肉禽市场,很多流动人口。以前人口管辖不像现在那么智能,流动人口一多,治安事件发生得比较频繁。我们破案全靠“铁脚板”。
我和所里的兄弟们一起,没日没夜地蹲守、走访、分析、研判,困了就用冷水洗洗脸,累了就和着衣服在办公室对付一宿,最终,破获了一起重大的飞车抢黄金案。
我就是憋着一口气,想证明只是手不好使了,我还有脑子和腿,哪怕被定为七级伤残,我还是能干好这份工作,对得起这身制服。当过兵的,哪个不是把疤痕当军功章?

是的,我当过兵。
从消防兵到警察,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基层。
1985年,我成为一名消防员;1995年转业进入公安系统,一干也有30年了。
现在,我在大队负责治安管理工作。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很多警务工作还得靠双腿和双手去做。

如今我巡逻经过万达广场,霓虹灯总让我恍惚看见20年前的西长街。当年带着钢钉臂摸排流动人口,用残掌画出的辖区平面图,现在还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谁家店铺消防通道堆货、哪个场所存在监控盲区死角,这些细节刻在骨子里比当年补的钢钉还要深。
前段时间给队里的几个新警培训,几个小伙子盯着我端茶杯时颤抖的左手。
“别瞅了。”我挽起袖子亮给他们看,“这是咱们这行最闪亮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