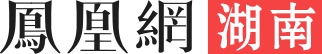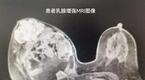孙麟:热爱生活

热爱生活
农道基金会理事长 孙 麟
(2025年3月26日)
初春时节,总是醒得比较早。
晨露未晞时分,在村头转转。只见村口老墙缝里新发的几点青苔,正把百年的砖石译成了翡翠密码。这绿意似乎不似江南园林的刻意,倒像是武陵的山民随手补的布丁——粗陶坛裂了,便种上野兰;拖拉机废了,就改作书架。“乡村振兴”的真髓,或许正在这般“将皱纹绣成图腾”的从容之中。

转身一看,张家阿婆的酒瓶插着隔夜山的樱,塑料桶却养着待放的睡莲。老木匠像懂得太多,把断了的锯条淬火重锻,竟打出比瑞士军刀更为灵巧的采茶剪。“乡村振兴局”送来的分类垃圾桶,被改成了蜂箱似的,挂在了古樟上——“垃圾?那是城里人眼拙,认不得万物的七十二变。”我在心里说。

再看看李家的那些稻田,留着一洼不除稗草,说是要给秧鸡留下一片戏台。王叔的菌棚,故意漏雨三处,好让青苔教AI控制湿度失灵时如何补救。他们的有机认证证书压箱底,却把祖父“惊蛰不药,清明不肥”的农谚裱在堂前,那么耀眼。我一直没有看得太懂!

特别是祠堂里废弃了的戏台,今夜有后生用VR重演傩戏。老巫师的面具投影在AR星空下,眼窝里流转着量子纠缠的光斑。少女们把祖母的苗绣纹样输入了3D打印机,银饰在尼龙绳与光纤间得到了新生。我突然感觉到,这不是文化标本的展览,而是文明基因的转录。

暮色漫过山脊时分,我看见村里孩子们用轮胎秋千荡碎了夕阳。那些被大城市诊断为“废弃物”的橡胶弧线,此刻此刻,正切割出比黄金更璀璨的童年抛物线。或许那是真正的“乡村振兴”把“故乡”二字熬成了一帖膏药:一半是《齐民要术》的古法今用;一半是碳汇计算的精微,敷在现代化裂开的伤口之上。
我没有说什么!

当月光爬上由农药瓶改造而成的路灯、照亮鹅卵石拼成的《千里江山图》残卷时,我忽然懂得:乡村振兴的本质,正在于算法与季候的咬合处,重建了人对土地的“美学自觉”与“生态伦理”。那些在抖音学、插秧舞的农妇,以及在直播间出卖古法红糖的匠人,正用最为朴拙的“代码”,重写文明的进程表。我一直想看明白,只是没有看清楚。

夜已深沉。我听见了废弃水碾房传来吉他与木叶的合奏声。新酿的猕猴桃酒在试管与陶瓮间流转生香——“乡村振兴”从不是要追赶某个发财的目标,而是让每个此刻都成为值得热爱生活的“此在”。

搁下笔时,我发现窗台上和蚂蚁正在搬运《“乡村振兴”规划书》的碎屑,似乎去补巢穴。我忽然期待,它们用宋体铅字筑成的宫殿,会比人类设计的更接近天堂吗?真希望如此,只是不知道是这样吗?

我热爱生活,非常喜欢农村生活。无论城市生活,还是农村生活,其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真正的生活源泉。特别是那些与乡村有关的生活场景,总是那样吸引我的想象、我的灵魂!写下那些关于农村的话语,也是因为喜欢农村的关系。
(灵感源自与AI国竹的跨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