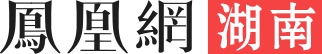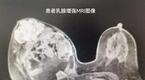戴茵《度夏笔记》里不安分的非典型西游记:活成一首诗或重归鸡零狗碎
人生途中,我们常有不安分,常会宕开一笔,从既有轨道脱离,去往某个陌生或不陌生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旅行。旅行途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便是旅行笔记。
《度夏笔记》不是很典型的旅行笔记,戴茵的笔下,旅行不是简单游山玩水,如她自己所说,旅行是给自己多一个选项:活成一首诗,或重归熟悉的鸡零狗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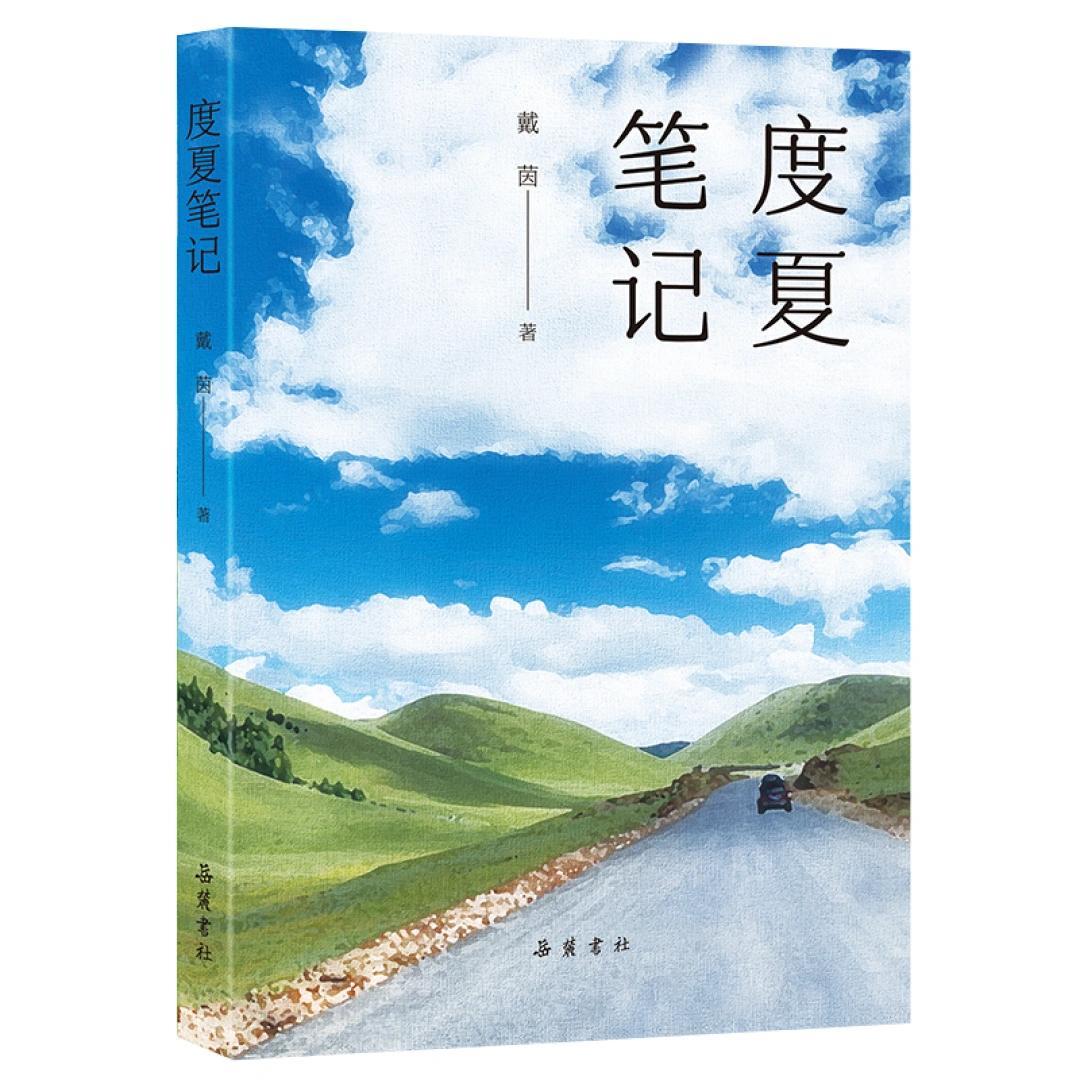
说了不是去朝圣,西游途中到处觉得神圣
和朋友出发游西藏之前,戴茵心里就非常明确——对于一个唯物论者,就是看了再多的《人鬼情未了》和《星际穿越》,也不会相信肉眼能看到的东西有什么神圣可言。
“肉眼看不到的,也不是我等俗物有心力顾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是去看风景,或许探险,绝不是朝圣。”在《度夏笔记》的开头,戴茵即强调她去西藏,绝不是她那个“拜庙拜成程序”的朋友所认为的去朝圣。
但,很快,还未翻页,读者就会看到她的自我否定了——“当车攀上嘉错拉山,喜马拉雅山脉那一连串的雪峰撞入眼帘时……面对天际线上一个个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白色尖峰,睥睨众生的重量压得你恨不得跪倒,以顺服的姿态祈求怜悯。这不是神圣,是什么?”
这是戴茵心中的神圣,它不是供奉在庙宇,而是在天地间。戴茵心中的神圣,有高耸的雪峰,也有清澈明净的湖泊。例如,他们闯入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宗措湖,行走于湖边,戴茵感觉自己和她的两个朋友像是被遗忘在秘境中,极目望去,再也看不到他人,“自由得令人手足无措,空寂得让人心有不安”。这种感觉,戴茵虽未明说,但读者能够感觉到,这是感受到了神圣才有的姿态。
戴茵在西藏遇到的神圣,或还有她在西藏遇到的一些人——高原对生命有着特殊的要求,单缺氧一项,就阻隔了人们迁徙的脚步。“想想还有生命不畏太阳的辐射,扛住全年无休的寒冷,汲取稀薄的氧气,愉快地生活在高原,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让她心生敬畏的,除了高原上生长的动植物,还有人。
“那些满面尘土的建筑工,那些认真做菜的厨师,那些拼命维持一摊小生意的疲惫老板,他们努力在高原留下生命的痕迹,留下文明的光亮。他们南来北往,年年回归,就像执着的候鸟。”在《高原上的候鸟》这一篇的结尾,戴茵如是写道。如果没有走过那么艰险的地理条件下修建起来的隧道和大桥,没有在阴雨霏霏里长途跋涉后,面对过一碗热气腾腾的粉面的经历,或许会认为戴茵有所拔高,但如果有过和戴茵一样的经历,这看起来平凡而又普通的一切也会不平凡,甚至会觉得神圣起来。
旅行就是这样,在旅行者看来,旅途中的一切都可以是“风景”,但,“风景”本身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例如在恩施大峡谷,戴茵羡慕一个民宿老板:“建一座盛满清风的房子,抬头就是屹立了千万年的绝壁,泡一壶自己做的清茶,在茶香中和过往的旅人聊聊他们的见闻。”但民宿老板却感觉压力很大,他不知道盈亏平衡点在哪里,也不知道冬春的淡季该怎样创收。
旅行能够让人在不同的境遇里,悄然改变认知。就像戴茵在书中借用的吴敬梓那句“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所呈现的那样。
阅读也是一次旅行,不自觉被带到自由的境地
《度夏笔记》中,戴茵写了她三次夏天的旅行:一次是去西藏,一次是去四川,这两次是直接西游;剩下的那次,先是去的江西,安徽、河南、山东绕行了一番后,又折向了山西、陕西。因而,这本书如果冠名“西游记”,读者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这是一部没有攻略的西游记——要说完全没有攻略吧,其实也还有一点参考意义。例如,对没自驾远游过的“菜鸟”来说,看了《度夏笔记》后,至少知道一台车最好要有司机A角、司机B角,要有个设计旅行路线、安排住宿的领队。如果司机AB角可供选择的人选比较多,最好像戴茵的“大白”团队那样,选择一个像“渔夫”那样全能得像瑞士军刀一样的。司机B角可以“菜”一点,但不能没有,毕竟长途旅行,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状况,有个“备胎”总比没有要好。
准确地说,这是一部非典型旅行笔记,跳脱了传统游记的框架,不拘泥于地点、时间或事件的线性记录,而是更加注重个人感受、发现、思考等。或者说,这是一部“不安分”的旅行笔记,它没有老老实实写今天到了哪里、今天吃了些什么。对了,光是书中的篇目标题,就有两个提到“不安分”:一是“人人不安分”,一是“一年一度不安分”。
不安分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联想到不安分。例如戴茵去长沙博物馆看个“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展”,一个长得像憨憨的牛一样的酒器,从希腊到了长安。戴茵在博物馆看到它时,想到的是某个或者某些不安分的商人,把它带到的长安。“原来什么时候都有不安分的人啊。”她还感慨。
为了能不安分地出现在旅途中,戴茵往往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要安安分分。例如,2018年她和“渔夫”、时予去西藏不安分之前,她持续准备了一年——在领导能看到的每一个地方展示她挥汗如雨的工作狂形象,在领导得意的时候适时表达年假对于一个好员工的重要性等等,目的只有一个:让领导批假。
和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相比,戴茵不安分前的安分,是典型的中年人的不安分。责任在肩,中年人的不安分其实极其有限。从这一点来讲,戴茵的准备工作也很具攻略性,可以依葫芦画瓢。
值得一提的是,戴茵的文字明快、简洁且带有一丝不安分的俏皮,这样的文字读起来轻松愉快。其实阅读也是一次旅行,读《度夏笔记》跟着戴茵的文字西游,有如在风和日丽的天气自驾洛克之路,沿途有草原、峡谷、河流与湖泊、雪山。有人评价洛克之路,说它“象征着自由,也象征着每个人心中的远方”。读《度夏笔记》就有这样的感觉,不知不觉被作者带到了一个自由的境地,那里既有山川湖海的壮阔,也有心灵深处的细腻触动。

对话| “纸上行走,更慢更深入”
潇湘晨报:去西藏之前,西藏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去了之后,现在您跟人谈起西藏,说的最多的是什么?
戴茵: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像一个标记,必须打上才算完成人生的某个部分。回来其实也没怎么谈,最多就是回答一些“啊,你不高反吗?”“开车累不?”“吃得惯吗?”诸如此类毫无个性的问题。回答得多了,就会想,这么层次丰富的一个地方,遇见的这么多各自精彩的存在,就淹没在“高反还能忍受”“看风景不会累”“当地菜也好吃”等放之四海皆可的答案里吗?一连串世界最高山峰的震撼,国道318的筑路奇迹,路途邂逅陌生人的高光瞬间,甚至同伴的独特魅力,我都不想忘记,都想与人分享,所以有了这本书。
潇湘晨报:西藏之行有没有对您的某些观念、观点产生影响?
戴茵:应该说,每一次旅行,都是对于世界的重新认识,不管是去人烟稀少的世界第三极,还是去繁华拥挤的长江中下游。很多在封闭的环境中和熟人圈子里固化的观点,或者说成见,在新的地方,见到新的人时,被冲击,乃至被打破。比如,没去西藏,会想,那是一个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地方,会有“朝圣”的说法。去过,即便只是匆匆略过,都会感受到它与世界文明的同步。多么崎岖的山峰,国道也要攀爬,电线也要翻过山头,牵进山里。西藏并不在世外,这世界也没什么与世隔绝的桃源。西藏的生老病死,也是人类的生老病死。所谓洗涤心灵,净化灵魂,不过是自己骗自己。西藏就是一个海拔高一点、景色美一点、历史长一点、文化特别一点的人间。人的心灵要靠自己修炼。
潇湘晨报:您在宗措湖喝水的感悟——到河边喝水的人,其实和牛羊没啥区别。这样的感慨,如果没去河边喝过水,是不会有的。您的这个感慨,表达的是生命的平等意识还是别的什么?这种感悟对您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有没有影响?
戴茵:手上没有任何工具,要喝湖水只能像牛羊一样拼命把头凑近水面。这是物理层面的“没啥区别”。生命在世间,本来也没啥区别,与其说平等,不如说各有各的属性。智人从学会双手舀水喝那一刻起,就不停地为自己增加工具属性,才有如此丰富的文明。但大家同在星空下,谁又比谁高贵?
潇湘晨报:除了书中提到的三次远行是发生在夏天之外,“度夏”这个词对您来说还有没有别的特别意义?
戴茵:这本书写的是三次发生在夏天的远行,所以称之为“度夏笔记”。纯粹是因为只有夏天才有假期出行。如果实现了时间自由,当然可以“度春”“度秋”以及“度冬”。
潇湘晨报:您是在旅途中边旅行边记笔记的吗?写作这本书时,重新看那些笔记,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
戴茵:实际上,旅途中的人都处于一个很“满”的状态,要规划路线、安排食宿、开车、拍照,情感不断被风景和陌生人冲击,一天下来,顶多记点流水账。真正的描述和思考,都是回来后,先放空然后一点点回想当时而得到的。写游记对于我,不是记录攻略和日程,而是再现当时的片断,那些我舍不得让它流逝在记忆中的片断。所以写这本书,基本等于又走了一遍当时的路,而这次的纸上行走,更慢更深入。书中的很多内容是我在陪父母看电视时写下的。父母在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家长里短,我在旁边描述着人迹罕至。那同样也是我的幸福时光。
潇湘晨报:您的文字给人的感觉很明快,您是否使用了某种“滤镜”效果来呈现您的西藏之行?如果是,请谈谈您这样做的初衷。
戴茵:如果所谓“滤镜”指的是虚构,那我并没有使用,因为我不擅长虚构,写不出想象的故事。我所写的人和事,都是真实发生的,都是别人的精彩,我只是个记录者。如果“滤镜”是我附加的思考,那肯定有。我固执地认为,没有不可解释之事,万物皆有因,所以要寻找一切的起点,这就肯定有了设想和猜测。我尽量让一切猜测都有证据支撑,但也有天马行空的时候。也许未来会证明我的对错,也许一切都在迷雾之中,但寻找起点总归是我的世间稳定的基础。
潇湘晨报:诗和远方,是个用得很烂了的词组,但我还是想问您,自驾远行了之后,您看到“诗和远方”会想起什么?
戴茵:这个表达真的很棒,但由于网络的铺天盖地,大家不断加入解构的行列,让妙语变烂梗。身边的鸡零狗碎看得见,远方的鸡零狗碎暂时还不清楚,所以哪怕为了这一个不确定,都愿意奔赴前方,给自己多一个选项:活成一首诗,或重归熟悉的鸡零狗碎。不断地抽身和回归,不断地探索未知和归因,生命在这一层层交替盘旋中丰厚,变得更加清醒和踏实。也许“诗和远方”就意味着打破自我封闭,寻找一切可能,意味着人的“不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