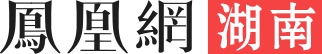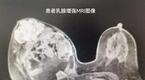谢宗玉:“实事求是”策源地,为啥花落岳麓书院,仅凭这块匾额吗?

岳麓书院,那束从历史照亮未来的光
(原载《中国作家》2024.9)
一、
那块黄底蓝字的匾额,静静挂在岳麓书院讲堂的檐梁上,已有百多年了。“实事求是”。隶书。笔锋凝练庄重,墨痕入木三分,能够想象得出,当初题匾者凝神静气的模样。这四字,他不是一般的看重呢。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说是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刘德喜欢在古籍中寻找真相。清嘉庆年间的考据派则承此而来,将“实事求是”当作治学宗旨:“为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
阮元是清代考据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系统地阐发了他们这个学派“实事求是”思想。之所以要重提汉代“实事求是”精神,就想用它来厘清儒学的发展历程。阮元认为汉代在老庄思想风行前,儒家经学研究比较纯粹,宋明理学则过于虚深,“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清代儒学“笃实敏求”,合乎“实事求是”。深思熟虑后,他对外宣称“圣贤之道,无非实践”,主张从“实政、实事、实行”中“求其是”,因此他也看重自然科学。
为了给考据派寻求治学依循,阮元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古代“实事求是”思想最完备的梳理者,同时也是最坚定的践行者。阮元既是著名学者,又是实干家,功绩斐然。其人曾任湖广总督,但岳麓书院“实事求是”这块匾额却并不是他题写的。
题匾者宾步程,比阮元晚生了百余年。当时是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纯粹的理科生。在永州东安读了几年私塾,就被望子成龙的父亲送进两湖书院。
两湖书院学风开放,文理兼修。创办者为张之洞,其时他正在搞洋务运动,急需一批有理科底子的报国者,所以教学自有偏重。这里的肄业生,多无心科举,而热衷留洋。宾步程也不例外,他凭借优异的成绩,于1900年被满清政府送往德国,进入柏林帝国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八年时间,宾步程足迹遍布欧洲二十余国,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已完全西化。
1908年,28岁的宾步程回到中国。他留着七分头,打着领结,穿着燕尾服,一双皮鞋锃亮泛光。按当时的说法,妥妥的“假洋鬼子”一枚。对腐败的满清,他已无丝毫归属感。在欧洲他就加入了同盟会,属老牌革命党人,曾筹款资助过孙中山。回国后他以粤汉铁路工程师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民国政府成立后,他的职务就一直跟工业相关。历任南京机器制造局局长兼火药局局长、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校长、湖南造币厂厂长、水口山矿务局局长等职位。
这样一位新潮理科学者,现在却焚香沐浴、聚精会神写下这四个大字,多少让人有些费解。一个古老的中国名词,为什么会被一个洋派学者这么看重?凭他已完全西化的学识,能悟透其中的博大精深吗?
事实上,他并不需要悟透。20世纪初,社会遽变,“实事求是”一词大行其道。可风行的并不是它的中国哲学含义,更多的是它的西洋“皮相”。因为那时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普遍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翻译成“实事求是之学”或“格致之学”。
所以,宾步程眼中的“实事求是”,更多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意思。怀抱实业救国梦想的他,深知“实事求是之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而匾额自古就是成风化人的重要媒介,对青年学子而言,具有潜移默化之功效。他书写此匾作为校训,高悬于讲堂之上,就是希望每位学子都能认真钻研,努力实践,追求科学,振兴家邦。
有意思的是,题匾时的宾步程,与“朱张会讲”时的朱熹,正好同是37岁。朱熹那时已誉满东南,相对各自所处的那个时代,宾步程的名气,显然要小多了。而岳麓书院作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想要在讲堂正厅题写匾额,非帝王圣贤不可。所以尽管朱熹当时已声名鹊起,但离圣贤尚远,他没敢在讲堂正厅题匾,只题了赫曦台、道乡台等一些碑名。
宾步程多年受西方思想熏陶,头脑中那根论资排辈的弦,已经绷得不是那么紧了。更重要的是,岳麓书院已不复古时的地位与名望。那些年,它屡被新学鹊巢鸠占,不停更换名称。这种变更,百年后回头来看,我们觉得这既反映了书院与时俱进的文化更迭,又展示书院海纳百川的思想包容。但在当时那个革命年代,它意味同过去彻底决裂。就是说,在新潮人物眼中,当时岳麓书院已失去了历史荣光,只是一所西式高等学校的校址而已。既然这样,那由这所学校的校长题写校训,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
其实早在宾步程之前,1914年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就把“实事求是”当作了校训。赵天麟23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回国后任教于北洋大学,5年后被任命为校长。很显然,赵校长所理解的“实事求是”跟宾校长差不多,带有浓烈的西方色彩。摒弃虚理,扎实干事,实业兴邦。类似于实用主义。
宾步程不但题写了讲堂匾额,还将孔子与韩愈的格言一起混搭,拼成一幅对联: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对一个读过古书的人来说,有点冒险。“嬉”是阴平字,严格来说,不好放在联尾。可宾校长才不管呢,只要能警醒学子,破了格式规矩又如何?毕竟那个年代,“破规”已是一种时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世纪初,随着儒学的式微,孔子的声望逐渐在向低谷跌滑,但他的这句语录,却被广泛引用。不过内涵与春秋时代已有很大差别。宾校长之所以将它悬挂在学校讲堂,是因为这话当时相当于为民族工业量身打造的广告语。

二、
一年后,也就是1918年夏天,一位青年书生在这块匾额前,凝神静思,伫立良久,心中有几许感慨,几分坚定,同时也有一丝迷惘。他就是25岁的毛泽东。那年他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五月,学校被军阀暂时征用。六月,杨昌济赴北京大学任教,临行前成功说服校方,将自己在岳麓书院半学斋的宿舍,暂时借给毛泽东。八月,毛泽东跟随恩师脚步,也去了北京大学。这就是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曾跟这块匾额朝夕相处。
际遇不同,导致三观不同。宾步程从小走南闯北,又在欧洲游历八年,这就注定了他看问题的西方视角,以及洋派思考方式。毛泽东则不同。他十七岁才走出韶山冲,二十五岁之前,几乎没出过湖南。长沙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尽管当时社会风气开放,西方思潮汹涌,但都浮皮潦草,人云亦云,且多自相矛盾,真伪难辨。毛泽东的“大本大源”,更多的是精研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形成的,而不是来自西方这些舶来品。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与宾步程相识。但宾步程的履历,毛泽东自然知道,所以也就知道宾步程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的真正含义。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已清醒地意识到,科学与工业,都只是术,而不是道,中国若是找不到自己的大本大源,无法解决形而上的思想问题,那么实业救国,也只是一句空话。那些买办资产阶级甚至可能借各种合资工业,将国家财富向西方转移。正因为这样,面对这块匾额,毛泽东才会感慨万端,百味杂陈。得益于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他当然知道这四个字的古老哲学意蕴。而且,他似乎还觉悟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当时他并没有拜访这位一身洋气的校长。
随后十月革命的胜利,沙俄暴政被推翻,邻国苏联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让梦想照亮现实的捷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陈独秀、李大钊成为共产主义先驱者,毛泽东开始接触并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直到这时,他才敞开心扉,正式接纳某些西方思想,并把它当作救世良药。但他的个人际遇和中国革命并非一帆风顺,直到将颇具中国哲学意味的“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嫁接在一起,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才让星星之火,燎原华夏。
本土“实事求是”与外来马克思主义的嫁接轨迹,得有一部学术专著才能讲清楚,但追溯毛泽东的认知历程,两者相融的重要节点,还是可以梳理出来的。
1925年至1927年,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意味他已将“实事求是”思想当作了自己改造旧中国的行动指南。1930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在他脑海已有清晰轮廓和框架。1937年毛泽东创作《实践论》,标志着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1938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用“实事求是”思想来规范党员,“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在1941 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详细界定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1943 年,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当作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并亲自题词。字体清健刚峻,笔锋铁划银钩,像一队蓄势待发的战士。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实事求是”被写入党章,这就意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式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也意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步于成熟期。
先是古为今用,后是洋为今用。凭借“实事求是”,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将东西思想合璧了。如果说宾步程、赵天麟等人偏重此词形而下的术,那么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则锤炼了此词形而上的道。并借此来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大本大源。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总结的:“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
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实践,真正做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对东方传统文化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沧海桑田,百年刹那。麓山巍巍如昔,人间日新月异。宾步程手书的匾额依然悬挂在书院讲堂,但“实事求是”一词经过时间的冲刷、酝酿、重塑与沉淀,已有了约定俗成的新含义。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岳麓书院,曾深情注视过这块匾额,认为岳麓书院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策源地。

三、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定论,跟宾步程已没有多大关系了。宾步程的字迹虽然还在,但此词不断脱胎换骨,跟当初作为校训的意思已相距甚远。宾步程本人也因食洋不化,水土不服,归国后高开低走。水口山工人暴动,他强势镇压,颇受舆论谴责,由此辞去矿务局长一职,之后这位洋书生担任的都是一些委员类虚职。他乐得轻闲,寓居长沙,著书立说,以理科书与工具书为主。如《无线电报简单机器学》《机算集要》《中德字典》《集古医方考》等。
而那时毛泽东已摸着马克思主义的石头,在蹚中国革命的汹涌暗流。宾氏的那些书籍,他自然没工夫翻阅,甚至都无法接触到。水口山暴动失利后,有一部分工人走向了井冈山。这大概就是他与宾步程之间最后的因果吧?
毛泽东对岳麓书院思想价值观的传承,走的是一条品质纯正的中国传统道路。这条路跟传道济民、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实干兴邦的思想脉络有关,跟周敦颐、张栻、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无数先贤有关,跟岳麓书院千年来永恒的价值追求和不断楔入社会、拯救苍生的进取态度有关。而种种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隐性呈现。
要把这些讲清楚,还得从岳麓书院的来由说起。
作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天生自带务实基因。这绝不是瞎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为解决问题诞生的。五代十国,湘人性情暴烈,习俗蛮陋,麓山寺和尚想借儒道加以引导,就在寺庙旁修建书舍,招收儒生,传授儒学。以期他们学成后,再去教化百姓。北宋初年,潭州知事朱洞将这些书舍从麓山寺剥离出来,创立了岳麓书院。
北宋初年,是民间书院创建的蓬勃期。北宋统治者对后周佛教恐怖的衍生能力记忆犹新,他们借助了周世宗灭佛运动后的便利,将尚处在废弃中的寺院和庙产,赐予官员乡绅兴办教育,以弥补官学长期以来的萎靡,民间书院由此大兴。
民间书院虽仍受制于官方,但与官学相比,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再全是冲着科考而去的禄蠹,少数人开始拥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与能力。岳麓书院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给“实事求是”种子储备了心灵沃土。
1015年,山长周式奉诏入朝,拜为国子主簿。宋真宗欲留他主讲皇宫,周式辞谢不受,返回岳麓授徒。宋真宗亲自为书院题写匾额,并让宫中秘阁赐送藏书。岳麓书院由此声名大振,天下传扬。
周式给岳麓书院的价值定位打下了关键性的桩子。为保持独立人格,他拒留朝堂,为书院后来的师生提供了一个保持本真、实现自我价值的新范本。这种拒绝,也为书院以后的发展,争得了更多的隐性自由,使得书院“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能自主开发,一脉相传。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道县人周敦颐开理学之滥觞。书院虽没有周氏涉足的记录,却专门设有濂溪祠祭祀他。程颢、程颐继承了濂溪衣钵,将理学发扬光大。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两人也从没来过岳麓书院,但岳麓书院的四箴亭长期悬挂两人画像,祭祠四季不辍。
理就是天理,是宇宙的至高存在。理无所不在,它既是世界本源,也是哲学的最高范畴,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向理、求理、析理,就是为了弄清世界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现在看来,先贤们虽不一定正确,凭借这些思想观念,也没有抵达大同社会,但他们求理向道的过程,却遵循了内心,并实事求是,虔诚如初。
南宋胡安国一生都在“康济时艰”,胡宏始终坚持“明体”“致用”,湖湘学派由此崛起。胡氏父子在湘期间,岳麓书院蒙难于兵祸,正处在沉寂期,但继承他们衣钵的张栻,后来却做了岳麓书院的山长,是他一举奠定了湖湘学派的江湖地位。
随着“朱张会讲”的成功,重修的书院再次成为南宋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以致“远近向慕,弦歌之盛,出于邹鲁”。回头来看,“朱张会讲”的意义不在于他们讲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热情。他们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问题公之于众,然后去芜存精,除异存同,达成共识,产生合力,让湘学与闽学交相辉映,继而成为席卷全国的时代思潮,最终被捧为官方意识形态。朱张的这一套组合拳,打得非常漂亮,效果极佳。对岳麓书院来说,这绝对是最为精彩的一笔。
就在这时,年轻的山长张栻为岳麓书院今后的发展定下了调性:传道济民,成就人才。张栻所说的人才,跟那些科举禄蠹是有区别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区别。
张栻曾明确表示,将青年学子聚在一起,不是单纯地为了提高文采修辞,去应付科举考试。而是要培养真正有道德、明是非、通时务、有能力的人才。他同时宣称“圣门实学贵于践履”,践履一词在这里,一是指“学以致用”,二是指在实践中检验学问的真伪。很显然,唯物求实、经世致用,一直都是岳麓书院遵循的根本。
张栻去世14年,朱熹做了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他一边修葺岳麓书院,一边在学子中倡导“格物致知”“先知后行”的学术研讨方法与理想实现途径,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逻辑。劝勉学子脚踏实地,“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
三百年后,王阳明之学在岳麓书院大行其道,他提倡“知行合一”,行就是知,知就是行。主张学子走出书斋,勤于实践,向社会求真知,于日常问真道。他与朱熹的知行观,虽有偏差,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想把事情做到实处,让言行产生实效。两人所抱持的态度,正是实事求是。
明末清初,作为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巨儒,王夫之主张“行先知后”“即事求理”“必以履践为主,不徒讲习讨论而云学也。”他的观点与书院前贤的思路也一脉相承。毛泽东曾长期醉心于王船山的思想研究,甚至在1920年至1921年期间,还住进了船山学社,书写了一揽子的“船山学”读书心得。“船山星火昔时明,莽莽乾坤事远征”,1957年长沙,在毛泽东宴请的聚会上,杨昌济生前的朋友即兴赋诗,首联就将毛泽东扭转乾坤的长征大业,与船山思想直接挂钩,可见当时的人们都熟悉两人思想的承继关系。
王夫之与前贤思想的细微差别,更多的是剖析事物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比如说,父亲把一颗红彤彤的野果塞进嘴巴,表现出一副满齿噙香的惬意模样,儿子看了一眼,跟着把一颗同样的野果塞进嘴巴。在朱熹看来,儿子所看的那一眼,就是求知。所以他是先知,而后才敢行,学着父亲吞嚼野果。父亲的行为与表情已让儿子作出了充分判断:此果不但无毒,而且味道极佳。
王阳明却认为,儿子非得让这颗野果入嘴下肚,才真正知道它的滋味,等过了一定时间,身体没有出现不适,才能判断是否适合自己。下次再要见到,就可以根据喜爱,把握摄入量了。整个过程既是行,也是知,所以“知行合一”。
对王夫之来说,父亲带着儿子出门尝野果的全过程,都是行。等儿子记住了这种野果的滋味、特征,以及生长季节与环境,甚至有了一套相应的寻摘与保存办法,这才是知。所以是“先行后知”。
这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重。细细想来,他们的知行观,其实还存在一种递进关系。从朱熹、王阳明到王夫之,对“知行”的解剖,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圆通。促使他们对同一命题的不断深挖,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精神。

四、
岳麓书院的另一巨子魏源是第一个睁眼满世界找优点的人,《海国图志》就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一系列紧贴时代的思想观念。从魏源开始,形而上的理论逐渐向形而下的技术过渡,这其实也是“实事求是”西化的开始。
将西方科技翻译成“实事求是之学”,虽不一定出自魏源,但一定受过他较大影响。后来无数学子之所以要漂洋过海,去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制度,魏源与他的《海国图志》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敢于承认自己落后、疯狂学习他人长处的思维与行为,其实就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时代体现。
等到宾步程这批人学成归来,把“实事求是之学”当作救国良药之时,离《海国图志》出版已整整过去了七十余年,那时宾步程等留洋学子甚至可能都忽略了“实事求是”的真正含义,以及它的历史渊源与本土化应用。
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也是岳麓书院的学子。有意思的是,他跟王夫之一样,就读其他书院,皆无法中举,一进岳麓书院没多久就金榜题名。可气的是,岳麓书院还要对外宣称,他们的主业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科考纯属无心之举。呵。
曾国藩虽然比魏源晚出生近二十年,但他对西学没有魏源那么深的认知,所以在“唯物务实”“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反而更能保持古代传统与东方特色。他追寻先贤足迹,将“实事求是”思想一以贯之地研究下去,并与时代潮流结合,探寻理论新路。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青年毛泽东的原话。尽管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批判过曾氏的局限性与反动性。但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的确是一名铁杆曾粉。
而“实事求是”,则是曾氏理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他曾多次提到“实事求是”,并对此词有过深刻思考,“夫可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事求是的“事”,难道不可以指物吗?实事求是的“是”,难道不是指理吗?既然这样,“实事求是”跟朱熹先生所推崇的“即物穷理”又有什么区别呢?
《讲堂录》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课堂笔记。借它可以窥探两人对“实事求是”的师承关系。《讲堂录》曾这样写道:“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涤生是曾国藩的号。这里所说的“实”,就是指实事求是。
种种这些,对毛泽东后来在党的根本路线上,将本土的“实事求是”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有着莫大帮助。换句话说,假如毛泽东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中国历史与传统思想,而是像其他人一样留学三年五载,那时再要将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反而更难。那样很可能不是两种思想的嫁接融合,而是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抹除与替代。
同样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的左宗棠,也出自岳麓书院,不过是出于岳麓书院里的湘水校经堂。此堂重视治事,因此左宗棠醉心“事功”,主张“弃虚崇实”。毛泽东曾将左宗棠划为“办事之人”,只能算作豪杰;而将曾国藩划为既“能办事又能传教”的人,因此可以豪杰圣贤并称。这种区分对待,避免了毛泽东过早看重“事功”,而疏于思想研究,对后来他“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帮助。用民谚来说,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浏阳人谭嗣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可他却继承了王夫之的道统,并且还是杨昌济的恩师。杨昌济早年肄业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师范的时候,他又在里面教书。而杨昌济又对毛泽东影响巨大。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拜读过谭嗣同的《仁学》,对他的“心力说”很是折服,并在1917年曾以“心之力”为题,写过一篇宏文。所以,谭嗣同尽管未曾就读过岳麓书院,但他的观念与书院众贤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
谭嗣同的主要学术观点“器体道用”论,就是对王夫之“天下唯器”与“尽道在尽器”思想的继承与发扬。谭嗣同认为:道依于器,则器存道存,器变道变。人既不能弃器,也不能弃道,却可以通过变器来变道。这就是“器体道用”论。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万物就像一个器皿,而大道就蕴藏在这个器皿里。以前都是主张改变事物的运行规律,从而达成改变事物的目的。谭嗣同在这里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想先改变事物的样貌,从而促使事物的内部发生变化。其实就是由量变到质变。只是那时中国还没有这个提法。
谭嗣同之所以要抛出这个观点,是在为维新变法寻找理论依据。既然一千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变革都难以改变历史现状,那不如先借西方的制度和技术,来改变中国现实之“器皿”,继而形成新的道统、新的思想。
如此立意,谭嗣同真是个天才。可惜戊戌变法太短暂了,谭嗣同还没来得及在现实社会中试验他的理论,就横刀向天,壮烈牺牲了。这也可以算作是“器体道用”变革的失败。事实上就算给他更多时间,他与他的同仁也很难将旧中国拽出绝望的泥潭。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那篇文章就是《心之力》。
文章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种种弊端,呼吁有志之士,振作心力,正本清源,“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 文章情感激荡,意志昂扬,精神振奋,视野开阔,目光犀利,理想高远,就算时隔百年,依然让人高山仰止,心驰神迷,恨不得跨山越海,去追随响应。
但话又说回来,在那篇文章中,青年毛泽东尽管能看清旧中国的乱象根源,也有改变它的意愿与心力,但当时当境,他并没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同学张昆弟曾在日记里,对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内心想法,有过描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苦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很显然,青年毛泽东对他没去过的西方世界是有误解的。在他看来,西方徒有物质文明,而缺乏精神文明。殊不知人家的精神文明只在内部通行,对于旧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他们只有无耻的掠夺。当然,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西学东渐是“器先道后”,科技与制度在先,理论与思潮随后。所以那时毛泽东只想先依靠西方科技快速解决经济问题,然后再来精心经营一个令人神往的东方精神王国,并推之四海。这其实就是谭嗣同“器体道用”的另一种尝试,也是当时社会很多仁人志士的想法,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必须相辅相成,才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中国。
之后,各类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如过江之鲫,有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辈们做尽了各种尝试,都没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子。直至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抛弃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原旨主义,在血与火的革命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同时,也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可以说,岳麓书院历代先贤所倡导的传道济民、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系列精神思想,就是湖湘文化的精髓要义,被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发扬后,从三湘大地出发,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席卷了整个中华。这才是习近平总书记说岳麓书院是实事求是思想策源地的历史依凭,而不是单凭岳麓书院大厅悬挂了那一块实事求是的匾额。
事实证明,岳麓书院的精神气质、哲学思想、学术传统和教育模式等,都在为实事求是思想的萌芽、形成、发展与成熟,提供了充分的养料与强大动能。
社会似潮,岁月如歌,岳麓书院所蕴藏的各种思想历久弥新,所培育的各类人才生生不息,新的时代,书院也将随着湖南在中部地区的崛起,踔厉奋发,与时俱进,重新焕发出独特魅力与璀璨光芒。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谢宗玉,文创一级,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毛泽东文学院院长,曾多次进入中国散文排行榜。有多篇文章曾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获过各类文学奖10余种 。著有16部文学专著:《时光的盛宴》《末日解剖》《草木童心》《涂满阳光的村事》《独自远行》等。
(转自微信公号“东篱笑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