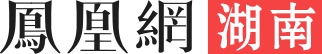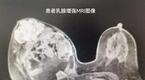王继斌:我的西乡美食记忆
盛夏时节,浏阳西乡蔬果大量上市。
灶下里,稻草秸秆被一把把塞进灶膛,烟囱里升腾起阵阵青烟。
砧板上,奶奶把磨盘一般大的南瓜切成大块,漆黑的铁锅里茶油在沸腾。奶奶说,南瓜就是要吃大坨,要先用油翻炒,有点焦也没有关系。
秸秆燃烧殆尽,餐桌上围坐的我们,每人面前摆上一大碗南瓜,粉糯、香甜。中间,是两大碗丝瓜汤、一盘鲜红翠绿的煎辣椒、一碗芋头茄子汤。
一天农活的疲惫、一天扯花炮筒子的单调、一天出诊看病的劳碌、一天学习打闹的声嘶力竭,都被这一桌子西乡菜消解融化。
这是我对浏阳西乡菜的童年记忆。
[ 美 食 ]

那时,我们的字典里没有“美食”二字。我们只有永远吃不饱的肚子。
田埂上带泥的芒草根、又酸又苦的“石灰”李子、涩得舌头麻木的柿子、刚从锅里捞出来还发烫的油渣、甚至泉水井里活蹦乱跳的小米虾,都是我们能入口的东西。
我们除了盼望过年,还盼望家里请木匠、篾匠、裁缝师傅,盼望村上有人拜堂成亲。
家里再怎么节约,请了匠人做事,长辈们总得要去集镇称肉买肉打酒,否则伙食太差传出去被人笑话。
记得有一年,家里请篾匠做晒垫,厅屋里满是竹子的清香。早上,奶奶把樟木饭甑里的糯米饭倒在新晒垫上,太阳一照,晶莹剔透。等糯米饭团冷了,放学后我赶紧抓一个塞进嘴里,软糯香甜有嚼头,这种感觉让人至今难忘。
村上有人成亲,小孩子们比新郎官还要高兴。新婚仪式最后一个程序是扔喜糖,我们把地上的水果糖抢到手塞进嘴后,急忙回到座位,迫不及待等着上菜。

西乡酒席喜欢用笋丝打底子,既照顾了面子又节约了里子。别人吃笋丝上的平肚、墨鱼丝,我总喜欢把碗底的笋丝夹满饭碗,对笋丝的特别爱好,一直延续至今。
浏阳西乡人喜欢以吃扣肉多少论英雄,他们斗酒时声音震天响,“一杯酒抵一块肉”,有厉害者,可以一口气吃完一个“扣肉面子”,这足以在村上成为热议的话题。
[ 西乡菜 ]

说起西乡菜,自然会说到“西乡狗肉”。镇头集镇往株洲方向的“洲名饭店”,去骨头的狗肉撕成条状经茶油爆香,与红薯粉丝同煮,用不锈钢盆盛装,撒上一把芫荽菜,引得食客如云。隔壁的普迹镇狗肉做法不同,在集镇最著名的“永红饭店”,这里的狗肉是带皮清炖。
地道的本地菜一般都物美价廉,但西乡的“扣羊肉”例外。用黑山羊肉做扣肉,“扣肉面子”是羊皮,羊皮下面是切成条状的羊肉。枨冲镇大厨邱海波说,一碗货真价实的扣羊肉,光原材料就需要一斤半,成本超过120元。

葛家是鸡肠子辣椒的原产地。“鸡肠子辣椒全席”是我的学生乡村大厨叶欢捣鼓出来的。叶欢到菜园子转一圈,十几分钟摘一篾篓清红相间的鸡肠子辣椒,用古井泉水洗干净。厨房里砧板上各种节奏的刀法响起、勺子与铁锅撞击摩擦声之后,“鸡肠子辣椒回锅肉”“鸡肠子辣椒煎豆腐”“鸡肠子青椒焖甲鱼”“鸡肠子红椒蒸土鸡”……
十个热辣滚烫的大腕上桌,一会儿主家就惊呼,高压锅里的饭怎么没了?
[ 乡间美食 ]

真正的西乡美食,不在酒店,不在饭铺,而在乡间。
唐明高老人是我的老姑爷,也是枨冲镇黑沙塘一片最著名的厨师。他早已离开人世,但他做的茴饼肉丸、虎皮扣肉存在后辈们的记忆中。跟着爷爷去老姑爷家过年,是我最期盼的事情。夜宿老姑爷家的夯土墙房子里,屋外寒风凛冽、屋檐上积雪足有两三寸厚。我枕着稻草秸秆填充的土布枕头,沉沉睡去。
邹伏桃老人,是我的叔外公,自己不但会烹饪各种西乡菜,更成立了一个班子,添置了可以开几十桌的碗筷餐具。每当村上有红白喜事,都可以在厨房里看到他指挥着自己的团队忙个不停。我的舅舅是乡村红白喜事的提调,他说西乡上菜要有规矩:平肚丝、墨鱼丝要先上,鱼要排第六七,狗肉不上正席。上亲没有吃完,帮忙师傅不能打散席爆竹。


[ 西乡做客 ]

在西乡做客的最高礼遇就是,主家邀请他会做菜的亲戚或者朋友,用最地道的食材,做一桌最热情的菜。
李旭家的青椒炒酸豆角、何建家的回锅肉、彭宏武家的豆豉蒸火焙鱼、邓雪阳家珍藏在冷藏室的特辣剁椒、温少鑫温少荣兄弟家的红枣糯米饭,是家宴上才能吃到的地道西乡味。
前不久,初中同学唐慧明邀请我们几个儿时伙伴到她家做客。桌上,鸡爪子是早上开始卤的、土鸡是后院满地走的、丝瓜是厨房边藤蔓上扯下来的、草鱼是50米开外的河里钓的、紫苏和薄荷是菜地野生的。
月出于东山之上,浏阳河里已经笼上一层薄雾,宾主言欢,不知不觉夜已深。
[ 岁月流转 ]

岁月流转,西乡美食,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还有这块地方上悲欢离合。
记得外婆每次见到我,都要到厨房里烧几把松针,给我煮一碗荷包蛋面。在她弥留之际,最想吃的是镇上的一碗米面。她不知道,这个外孙,曾带着他的小伙伴,挖过她后院山谷里的红薯。
记得每年正月初一的早饭,奶奶都会炒青菜、煮芋头,讨个一年“清气”好事“遇”头的彩头。她中风离世前,留给我的一句话是:将来你参加工作有钱了,要买点好吃的给我。她的孙子参加工作了,却从来没有机会给奶奶买吃的。
陈晓卿说,吃着吃着就老了。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