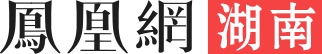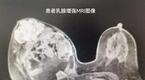马珂:逐梦年华(散文三题)


独家抢先看
海南《椰城》文学月刊2023年第12期
文学社
入冬,饮茶成为一种心仪的消遣方式。随意坐在书房里端起茶杯细品佳茗,就有许多值得留念和回味的经年旧事在脑海里叠映浮现,一如撒落在生命中的细碎阳光,在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泛着温暖的光芒。其中便有我年少时在故乡追逐梦想的美好年华。
上世纪八零年代,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个不可复制的炙热时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仿佛约好了似地把文学创作当成了各自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就连当时报刊上登载得密密麻麻的《征婚启事》,“爱好文学”也是博取异性青睐的重要资质。一时间,各报刊争先恐后地办起文学刊授或函授中心,随之便是层出不穷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遍布祖国的工厂、机关、部队和学校。在那个为文学疯狂的年代里,仿佛种子炒熟了,只需丢进土里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这股热潮的冲击下,正值年少的我,也怀揣梦想加入到爱好文学的亿万大军之中。尤为难忘的,是由我牵头,纠集一帮文学青年在家乡一座山区水电站组建文学社团,激情昂扬地拉起“星湖文学社”大旗,集资出版铅印文学小报的经年旧事。
请让我把时光倒回到1986年的春季。
当年爸妈为鼓励和我一样热爱文学的二弟马晶能在创作上有所进步,想出个“奇招”,设立了一项“家庭文艺奖”。条件是凡在地市级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一篇(首)文艺作品者,得奖金10元;在省级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一篇(首)者,得奖金20元;在中央级报刊公开发表一篇(首)文艺作品者,得奖金40元。那年夏天,湖南省怀化地区文联组织作家来我们所在的山区水电站召开创作笔会,文联副主席谭士珍老师(长篇小说《朝阳花》执笔者)知道这件事后,写了篇题为《沅陵一职工设立家庭文艺奖》的稿子发表在《湖南文化报》上。一时间,百余名省内外文学爱好者根据稿件开篇所写的“沅陵县岩屋潭水电站职工马绍发有三个儿子,长子马珂、次子马晶均热爱文艺创作”透露的地址,先后给我们写信,要求建立联系。读着文友们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我的脑海里生出一个念头:把这些与我一样初学写作的文学青年纠集起来,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当年我们居住的水电站是个小湖区,我把即将加入文学社团的文友们想象成一颗颗冉冉上升的文学新星,起了个“星湖文学社”的名称。我自任社长,打算通过社友集资的方式筹集资金印刷社刊。那真是个人人都对明天和未来满怀信心的纯真年岁,邀请加入星湖文学社并集资编发铅印文学报纸的信函寄出不久,回信和汇款单就像雪片般纷至沓来。尽管每人每年仅象征性地出资5元作为印报费用,但百余名素不相识的文友所给予的信任和支持,却让我受到了无以言表的巨大鼓舞。经多方努力,有关部门批准了我们出版铅印文学报纸的申请,给星湖文学社下发了报刊准印证。之后我利用去邵阳市参加湖南省歌词创作笔会的机会,请时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的谷曼老先生为我们即将出版的八方诗友短诗辑《诗苑》题写了刊名,同时还邀请辽宁《当代诗歌》月刊副主编阿红、我省诗人于沙和怀化地区文联副主席谭士珍等老师担任文学顾问。
1986年秋,星湖文学社铅印出版的第一期四开报纸《诗苑》与文友见面,刊登了辽宁、北京、上海、内蒙古、新疆、陕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几十位文学爱好者的短诗,印刷了五百份。报纸出厂后,我们在给每位社友和作者赠寄报纸的同时,还给多家报刊社寄送报纸,希望编辑能从中选发某些作品,并与国内二十余家诗社、文学社进行交换。为造声势,我们还拿出一百来份报纸在当地赶集的日子摆张小桌按每份两角的工本费当街售卖,同时也结识了一批本地文友。那个时候,我和马晶居住的房子里到处堆放着来自各地的信件,仿佛一个邮政分所。而我们感到最亲切的人就是头戴绿帽的邮递员。每每看见他们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在路上不辞辛苦地奔走,就对他们肃然起敬,想象着那个鼓胀的帆布邮包内是否装着属于我们的邮件。
星湖文学社的第一期诗报《诗苑》让我们拓宽了视野,了解到更多的文坛信息。于是,我们将第二期社刊改为既发短诗又发小散文、小言论、小小说的铅印文学报纸《芨芨草》,资金不够就自己贴钱印刷。在山区水电站一期接一期出版的报纸,像文学大花园里一朵朵细小的报春花,清癯的根,驴蹄似颤巍巍地举起坚毅。
基于少年时代的追求,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一家省级报社工作。在采写和编辑稿件的同时,不忘当年挚爱的文学创作,在省内外报刊公开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后又被报社调至文学副刊版任责任编辑,逐步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
笔 会
在我近三十年的媒体生涯中,曾有过十五年在海南和北京做报纸的工作经历。其间有十多年时间任职省部级报纸的文学副刊责任编辑,编发过诸多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也多次应邀参加各种级别的文学笔会。可记忆中难以忘怀的,还是我初学写作时与二弟马晶在家乡湖南沅陵参加的两次文学笔会:一次是应本县官庄区杜家坪乡文化站《林花》文学内刊主编袁因老师的邀请去林区参加改稿笔会;一次是应怀化地区文联副主席谭士珍老师的邀请参加地区文联在官庄镇举办的文学创作笔会。
记得那是1984年初夏的某天,二弟马晶肩挎一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色帆布挎包进县城开会,经人介绍认识了官庄区杜家坪乡文化站《林花》文学内刊的创办人袁因老师。当袁老师悉知我们兄弟俩都酷爱文学,高兴地表示愿意与我们在文学之路上结伴同行。袁因老师较早就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他原本是一名税务干部,却义务承担起文化工作者的重任。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为杜家坪乡文化站创办了一份铅印文学内刊《林花》杂志,给山区文学青年开辟出一块刊发习作的园地。二弟回来后兴奋地与我谈起这些,兄弟俩都感到异常兴奋。夜色在马晶兴致勃勃地叙述中越来越浓。那一夜,我们都在那张窄窄的木板床上失眠了。几天之后,一本带着墨香的《林花》铅印刊物寄到了我们手中,两兄弟争相一睹为快。读着杂志上一篇篇带着泥土芳香的本地作者作品,仿佛有种超常的力量,鞭策着自己一定要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不久我给袁老师寄去一组小诗,马晶寄去一篇小说。很快就收到了回信。袁老师对我们的习作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要我们改好后再寄他收。那年,我和马晶的文稿都在《林花》文学内刊上刊登了,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那以后,我们两兄弟常给《林花》写信投稿,我的诗歌《春往故乡行》还获得了《林花》第二届创作奖。有了这番历练,兄弟两人的作品先后在公开报刊上发表。
第二年初春,我和马晶同时收到《林花》文学内刊邀请去我县最大的林区杜家坪乡参加改稿笔会的信函。首次受邀参加笔会的我们心潮澎湃。人生中的第一次,对任何人而言都是难忘的记忆。
带着欣喜与匆忙,我们各自背上装着手稿和衣物的背包,兴致勃勃地从住地搭乘一辆进林区装运木材的大型敞篷货车向目的地进发。货车在飞檐峭壁的盘山公路上冒着浓浓的黑烟奋力前行,时不时发出“轰轰”的加油声,我们坐在露天的货运车厢里沿途欣赏着公路两旁繁茂的树林和盛开在悬崖上的各种鲜花,心里想着又能在改稿笔会上结识到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友,心情异常欣喜。
笔会安排在杜家坪乡政府举行。与会的二十多名男女作者均为本县文学青年,而且都在《林花》文学内刊上刊发过习作。笔会组织者袁因老师忙前忙后地给大家安排好食宿后,于当晚在乡政府礼堂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朋诗友见面会。文友们一个个登台自报家门并介绍自己的创作经历,热烈的掌声不时在会场响起。一帮拥有共同爱好的年轻人济济一堂听着身边人的发言,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改稿会于第二天正式举行,大家先是把自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稿拿出来一起讨论,然后各自回到房间修改。此次笔会共举办了三天,最后一天是参观国营齐眉界林场并在林场投宿。林场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介绍了林场概况后,带我们参观果树林。时值百花齐放的春天,所到之处繁花似锦,白的梨花红的桃花漫山遍野,真不愧走进了花花世界。
尤其是晚上在工棚里住宿,满鼻的花香陪人入睡,清早被叽叽喳喳的鸟儿叫醒,起床后发现周围的花草吸收了一夜的甘露不仅长高了许多,花枝上也冒出了更多的花蕾、绽开了更多更鲜艳的花朵,处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改稿笔会结束后,文友们各自把修改好的稿件交给袁因老师,袁老师择优在《林花》上刊登。
第二次是到官庄镇参加怀化地区文联举办的文学笔会,与会者近百人。不仅有怀化地区文联和沅陵县文化局的领导,还邀请了《湖南文学》月刊副主编王以平等老作家给文学青年授课。当时有怀化、麻阳、溆浦、沅陵等市县的文学青年应邀参加。大家住在镇上的招待所,晚餐过后,平时难得一聚的文友三五成群地在官庄街头结伴游走,你一句我一句地畅谈文学、畅谈人生、畅谈理想、畅谈爱情,亢奋得彻夜难眠,生怕时间过得太快,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在那种激情四射的氛围中,仿佛青春没有地平线,仿佛伸手就能触到天。
当时正值夏日,某个黄昏,当地文友邀请去镇旁的小溪游泳。男青年纷纷参与。在流经官庄那条清亮的小溪里,年轻的文友们尽情嬉闹,还有人捉到了螃蟹和小鱼,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笔会中也有一见钟情的青年男女,他们避开人群,悄悄寻找一处静谧的地方促膝而坐。一如前苏联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描述的情景: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默默看着我,不声响……
光阴荏苒。一晃荡,这些历历在目的情景如今都已成为三十年前的往事,袁因老师也已离开我们驾鹤西去。但我在沅陵官庄参加的两次文学笔会,却在生命中显得弥足珍贵。
圆 梦
对电视的好奇,是从我上中学的时候开始的。
学校附近有家军工厂,常在周末放电影。某次在电影院前的玻璃宣传栏中,我看到一篇用毛笔书写的文章:《我们什么时候能看上电视》,并配了张电视机的插图。当时我生活在湘西沅陵一个崇山峻岭中的小乡村,对山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电视”这个新生事物便深深留存在了我的脑海中。
第一次看电视是1984年,搭帮改革开放时期实施的平反冤假错案政策,蒙冤下放农村十八年的父亲得以平反,带领家人离开山村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爸爸所在的单位食堂,每晚都播放电视节目,老老少少的观众早早就自带凳子去占地盘。那个时候我才对电视有了直观的认识。也是从那时起,我有了“进电视台工作”的梦想。
应该说,我们这代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学毕业我又赶上了海南开发的高峰时期。于是一路哼唱着三毛的《橄榄树》登上南下的列车,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名弄潮儿。凭着一定的文学功底,我被共青团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青年报》录用为记者。在那个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大特区里,我把一腔热血全然融入到本职工作当中,采写了一系列反响强烈的长篇报道和纪实文稿。纪实特稿《戴碧蓉的风雨人生》发表后,原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给我所在的报社写信说,“马珂采写的长篇特稿读后让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是湖南人,戴碧蓉的事我早就知道。我已经把文章剪下来寄给了中国残联的有关同志。”此文后来还被《中国青年报》刊发。
汗水换来的业绩还给我带来新的转机,海南省政法委机关报《海南法制报》老总找到我,力邀我去“法制报”工作。并把我带到时任省司法厅厅长习正宁的办公室。习厅长微笑着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打电话叫来干部处处长,要他尽快办妥我的相关手续。进入《海南法制报》后,我在担任报纸版面策划、文学副刊责任编辑的同时,还采写了大量的“本报特稿”。当我带领实习生马凯采写的长篇通讯《英雄不应再流泪》见报后,除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还被《特区文摘》、《记者写天下》等多家报刊转载。因文章涉及到个别部门,使我受到威胁。我把情况反映给报社领导,领导及时向习厅长作了汇报。几天后,由省司法厅牵头,召集海南省综治、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威胁我的部门负责人一起,召开了“《英雄不应在流泪》座谈会”,会议由习厅长主持,与会者就文章提出的“如何让见义勇为负伤者流血不流泪”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海南法制报》还以《真实 感人 遗憾》为题,用整版的篇幅对座谈会的内容予以报道。使我作为一名记者的权益,在习厅长和报社领导的关怀下得到了有力维护。
记忆深刻的还有对前往海南参加活动的老一辈艺术家:如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故事片《早春二月》、《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中的男主角孙道临,故事片《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侦察兵》男主角王心刚和父辈喜爱的大作曲家王洛宾等人的采访。
因我儿时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农村,文化生活异常单调。每年只有县里和公社派人来小山村的晒谷场上放十几场露天电影。电影可是山里孩子的兴奋点和最爱。同样的影片,往往要追好几个村子反复观看,烂熟到银幕上的人物还没把台词说出来,一群看电影的孩子就齐声说出台词的程度。而童祥苓、孙道临、王心刚等塑造的银幕形象,早已铭刻在我的心底。儿时只能在银幕上看到的人物,如今就面对面地坐在眼前接受访问,那种感受的确非同一般。记得在海南宾馆采访孙道临、王文娟夫妇时,我说起一群孩子打着火把赶好几里山路到相邻的村子重看王文娟老师主演的戏曲电影《红楼梦》和《追鱼》,夫妻俩都感慨不已。采访结束,孙老师主动给我留下住址和家里电话。我把采访两位老人的样报寄出后,那年春节还收到他们从上海家里给我寄来的贺年卡。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在海南媒体工作了十年有余,采写发表了百余万字的各类作品,多次获得海南省好新闻奖和国家级奖项。之后,我北上京城,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红色专访。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彭珮云、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以及刘少奇之子刘源、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等作了深度采访报道。几年后我返回老家湖南,加盟到湖南电视台,从纸媒转型到电视。除完成本职工作,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创作了多部电视文献纪录片和影视剧。实现了少年时代“进电视台工作”的梦想。
作者简介:马珂,生于湖南沅陵。在海南、北京历任省、部级报刊记者、编辑、执行主编,后转行至湖南广播电视台从事电视工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文艺家》《瞭望东方周刊》《散文百家》《湘江文艺》《星火》《天涯》《湖南日报》《海南日报》等发表各类作品近两百万字。《年少在乡村》(散文三题)获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二等奖,散文《又是一年秋风至》入选全国通用版小学《语文》同步阅读教材。多篇散文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青年文摘》《海外文摘》等报刊转载。参与创作、编著书籍和拍摄电视纪录片、影视剧多部。
来源:海南《椰城》文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