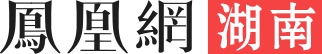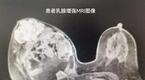上野千鹤子:日本近代家庭的崩溃,从何时变得显而易见?


独家抢先看
在历史的某个时间点开始的事情,在别的时间点迎来终结。在现在这个时期“近代家庭”论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家庭公然出现裂缝了吧。正因为感到就在眼前的家庭的自明性在崩溃,一个追溯性的问题——“这个崩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像现在一样显而易见的呢”——就浮现出来了。

“近代家庭”的概念
“近代家庭”是一个记述概念,而“近代式家庭”是一个规范概念。前者不过是在近代这个时代里形成的、具有一定特征的家庭的历史类型。
1994年联合国家庭年的标语是“从家庭开始的小小民主主义”,但实际上家庭里没有民主主义。家庭是性和世代不同的异质度很高的小集团。在家庭中,权力和资源被不均等地分配着。年长的男性统治支配着年少男性和女性的父权制概念,也适用于近代家庭。
家庭论的论者们主张,在“家”制度不复存在的战后家庭,父权制等等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最小家庭的核心家庭里面,依然存在着丈夫的专权支配这一家长“丈夫”制度。父权制这个概念,一旦使用的话,对表现家庭内部女性的经历,是非常有效的。由女权主义再次定义的近代“父权制”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并扎根下来。在我出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地平线》一书的1990年,围绕“父权制”这个概念,学界发生了论争。之后,作为替代父权制的概念,人们提出了“性别秩序”和“性别制度”等概念。然而过了二三十年再来看看,其中顽强存续下来的是“父权制”这一概念。我觉得这个术语具有的如实描绘统治女性的压迫性结构,是很容易被理解的。
家庭的“破坏者”
女权主义的家庭研究,打开了被视为“爱的共同体”“隐私的城堡”的“近代家庭”的盖子,一一揭露了其中的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这种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压迫女性的结构。正如家庭史学者说明的那样,所谓近代解放的“个人”,是在父权这个名下的“个人”。倒不如说,在家长管制下的“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变成了法律不介入的“无法地带”。
后来我在《差别的政治学》一书中论及国民国家的市民权有多少是与近代家庭的父权制权力结合在一起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个相同的问题,女权主义法学家们论述说:“所谓私人领域,那是公共制造出来的东西”(琼·斯科特);“不介入也是一种介入”(弗朗西斯·奥尔森)。在公民社会是犯罪的事情,在私人领域即便是做同样的事情,也不会认为是犯罪。就这样,我们很早就知道,无论家庭暴力还是对小孩的虐待,在家庭中都肆意妄为地进行着。
所谓“私人领域”,并非从公共领域营造的避难所,也不是防波堤。那仅仅是对家长、丈夫而言而已。为了揭露私人领域的压迫和暴力,女权主义者领受了被叫作家庭的“破坏者”的不应得的批评,但是女权主义并没有破坏家庭,而是家庭早就已经破碎了。女权主义只不过是把这个事实暴露在日光之下而已。为此,它要承受关于家庭的各种各样的“神话”的抵抗。这是因为家庭以往被如此理想化和神圣化了。
家庭的变化
在卷首收录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是本书的重点。这篇文章一边原理性地提出家庭的概念,一边提示了理论与实证相交叉的方法论,家庭社会学家高度评价其为“现象学的家庭研究”。《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这本书获得1994 年度的“三得利学艺奖”,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得到好评的缘故。
这篇论文把家庭是没有定义的概念作为前提,也反映了我自身深深地受到人类学的影响。用结构主义来说,“所谓家庭”,既不是“人们称为家庭的”之上的东西,也不是其之下的东西。我们把这种家庭意识叫作“家庭自我认同意识”。
本论文在方法论上很有特点的是,把家庭当作个人的集合体,使属于个人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之间的偏差变成能够实证的事情。家庭并不是集体式的人格。自我认同意识只归属于个人。家庭发生变化,意味着构成家庭的每个个人发生了变化。文章把使家庭成立的要因中的血缘与居住、形态和意识分别放在四个象限中,通过找出非传统的家庭来探讨家庭的变化,就像题目所示,预兆了后近代家庭的“走向”。我们采用了配合从理论图示得出的、寻找效果来验证经验性事例的方法,把以往“不能被称为家庭的家庭”,亦即边际家庭(borderline family)当作研究对象。这个边际,后来接续到“家庭的临界点”,亦即“家庭走向哪里才不算家庭了呢?”这个问题。
现在回过头看,可以说本论文的预测力是很高的。血缘与居住不一致的“家庭”(合租和集体生活)、形态与意识不一致的 “家庭”(事实婚姻夫妇、同性恋伴侣、再建家庭等)连续不断地出现。同一时期,反对把这样的边界性的“家庭”称作“家庭”的动向也出现了。1997年社会学家山田昌弘执笔的家庭科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时,理由之一,就是论述“家庭的多样化”的部分。在听到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员把教科书中有人“视宠物为家庭成员”的部分裁定为不恰当的时候,我哑然失笑:我们的研究早就实证了“宠物是家庭成员”的事实。
性革命的动向
判断某个社会有没有经过“性革命”的两个人口学指标,我们可举出离婚率的上升和非婚生子出生率的上升。离婚是与结婚、与爱相分离的指标,而非婚生子出生率是与结婚和生殖分离的指标。性革命使性与爱的分离、性与生殖的分离、结婚与性的分离成为可能。
“浪漫爱情意识形态”的解体,在日本也进行着:同时期的出生率的低下和婚姻率的下降,爱与性、结婚与性的分离,也在日本的年轻男女之间发生着。非婚生子出生率,是婚外性行为及其意料外的妊娠结果的指标,但是在被称为“流产天堂”的日本,看起来不仅婚外性行为很活泼,而且意料外妊娠可以通过人工流产而被解决。另外,离婚率是显示婚姻不稳定性的指标,但是与一旦不结婚就无法离婚的情形不同,所谓不婚,可以说在结婚前就已经选择了“婚前离婚”。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极端的低出生率跟非婚生子出生率的低下、不婚率的高百分比与离婚率的上升,岂不是功能性等价的指标吗?这么考虑的话,我们可以说,日本和其他的先进工业国一样,以其独特的方式经历了性革命了吗?
事实上,像性行为的低龄化和平常化、婚姻稳定性的崩溃等,今天从很多方面均可视为“浪漫爱情意识形态”解体的现象,在日本也能观察到。这种变化变得具体而可观察,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94年出版的本书,大概以70-80 年代的日本社会现实为考察对象,后来回顾,其实在出版那个时点,“近代家庭”崩溃的预兆已经俯拾皆是了。
是“ 后近代家庭”还是“后家庭”呢?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增订版),[日]上野千鹤子 著,吴咏梅 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出版](https://d.ifengimg.com/w1080_h1572_ablur_q90_webp/x0.ifengimg.com/ucms/2023_09/DB42040A571A617FF9CF320BF0F0481B2183C970_size137_w1080_h1572.jpg)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增订版),[日]上野千鹤子 著,吴咏梅 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出版
本书初版至今已25 年。“近代家庭”解体的预兆,现在正在变成现实。
果真如此的话,接下来的问题是,前面等着我们的是“后近代家庭”呢,还是“后家庭”呢?如果是前者,“近代家庭”即使没有了,也不过是变成了其他的家庭。若是后者的话,被称为“家庭”的现象,就从社会退场了。
人类历史的知识教给我们,不存在缺少相当于家庭的小集团的人类社会。因此,如果是“后家庭”,就意味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以往从未经历过的阶段。生殖技术的技术革新,暗示了像代理孕母生产、订制婴儿那样,生殖是能够人工控制的。然而,在以往的历史中,像人的养殖、“儿童牧场”这样的主意并没有过成功的尝试,将来估计也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人要成为人的过程,要花费的成本过高,无论市场化还是公共化都实现不了。岂止如此,生殖技术甚至反过来为强化血缘主义而被采用。已经接受了没有孩子的不孕夫妇,以往会被责备说,“还有生孩子的手段啊,为什么不努力试试?”现在,人生人的再生产制度,在家庭以外的机制中看不到。
少子化的背后有着婚姻率低下的背景。也就是说,组成家庭的人们和不组建家庭的人们,正在发生分化的现实。在其背后,有着阶级、性别、性欲、人种等差距。不组建家庭的人们,亦即由单身者构成的社区,我们能说他们是“后家庭”的社区吗?在这种社区中人们的人际关系和性欲的真实状态是怎么样的?……现在还未得到解答的问题还会出现得更多吗?
(本文摘编自《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增订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标题为摘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