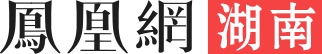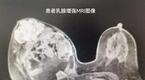专访|诗人李建春:从大冶到武汉 游历四十载


独家抢先看
在很多诗人和学者看来,李建春是第三代诗人以降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觉将自己放在传统的大宇宙,以及语言/思想的谱系中寻词觅义。陈东东如此评议李建春,“有天生的诗人,有命运的诗人李建春给自己诗集题名给出的示意,显然,他更认为自己是命运的诗人;然而,就像他给出的另一部分尤其重要的示意——他力图是一个改造的诗人,既以诗改造那个命运的诗人,进而也去改造诗本身。”

诗人、学者李建春
1990年代,李建春走出校园,没有去单位报到,而是下海广州。他的诗歌迅速生长,“睥睨天下”,他结识了“天下”诗人,获得了不少嘉许,比如刘丽安诗歌奖。在从事当代艺术评论之余,李建春还参与编辑民刊,比如《文学通讯》《向度》《声样》,为1990年代诗歌留下了重要的几份档案。至今,李建春为他的前代、同代、后代人撰写了大量书评,比如王家新、丁丽英、庞培、陈东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花期。李建春认为第四代诗人发源于19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时代以前,却又在媒介的跃进、时代氛围的变化、身份的保持和跟进的心态中,被几乎蒸干了骨髓。“第四代诗人的写作年轮最扭曲、光谱最广,但是独特性也最难辨认。因此只有终极的、时间的辨认,即审美辨认,而审美、时间性超越于道德和功利的价值。”李建春在一则断片中写道。
自198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李建春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武汉,“维护和磨练自己的不合时宜”。武汉的文艺圈在中国省会城市中颇为亮眼,这主要得益于历史文化积淀、区位优势(中南大区所在地),以及1978年以来的文化政策。以李建春就读的武汉大学为例,刘道玉在1980年代任校长期间开辟了中国大学的改革先潮,至今积累了很多文化成果。1999年至今,李建春先后供职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学院美术)》、湖北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2021年,两卷本《李建春诗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冶到武汉
澎湃新闻:您比较明确地提出,您的基本观念来自中国农民的价值观,他们的荣誉感、生活直觉。但实际上根据资料,您生活在农村的经历大概从到武汉读大学就结束了,此后的人生您如何保持这样的农民经验和价值观?是凭借父亲、祖父等血脉的关联吗?
李建春:我从大学里面学到的所谓现代性就是叛逆自己的农民父母,越是好大学越叛逆。特别是作为接纳了五四血脉的优秀文科生,我学会的,用农民的话说,就是不孝。我骨子里是一个孝子,我是家中长子,后面有两个弟弟,我是学历最高的。考上武大后,我不仅没有“一把黄伞照家人”,反而给他们带来困惑。直到31岁,我的儿子出生,才稍稍改变。
34岁时,我的父亲查出肝癌,一切都太晚了……我是那时候成为孝子,成为父亲的安慰和家庭的支柱之一。精神上强调作为农家子身份带有愧疚、补偿的成分,父亲逝世前后我写出《命运与改造》等长诗。从1997年后回武汉工作,我几乎每月都要回老家一次,因此我与农村的关系并不浅薄,春节、清明节从不无故不回。
在中国传统中,士农工商,士可以来自农,农民通过科举考试可以进入士阶层,工和商没有科举资格。我接触到的老一代农民,不管他们事实上是什么地位,在现代政治中被描述成什么,他们对国家的参与感、责任感都很丰沛,这让我震惊,我在《六爷》这首诗中提到过。当然,这不是主要的。
在诗学上我考虑与全球化相对的地域性。我收集过本县和附近县的县志,研究过本地方言,发现最土的、不可写的口语原来是文言……我有过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最后写成的是长诗三部曲《卧游录》。在激进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强调地域性和传统文化,至少在疫情发生之前是这样。中国农民的荣誉感、生活直觉指的是这些内容。
澎湃新闻:在地图上显示,您故乡所在地胡铁村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村,离镇中心也比较远。它和周边的村庄有生活和经济上的联通吗?
李建春:当然。村与村之间存在姻亲的关系,我有很多亲戚,尽管我不走亲戚。我妻子家与我家是一个大队的,隔一条季节河虬川。
澎湃新闻:您的诗歌,尤其早期诗作和长诗比较倚重经验和实景,您也强调,诗歌应留生活现场的印迹,保留它的文献性。而根据资料,大冶市(曾为大冶县)地理文化传统非常好,历史悠久,经济也不错。可否说,您诗作中的中国地理主要取自大冶市?又可否认为它带有虚构的成分?
李建春:我生活的镇与大冶市的距离与到武昌差不多。我只是读大冶一中时在大冶县城生活了三年,那时我和高中同学都来自大冶市(县)以及周边,所以我遗憾与大冶住得太远,虽然我的两个弟弟的家庭在大冶和黄石。我没有运用关系亲密的高中同学到我的诗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如果我生活在大冶市边,我会与劳伦斯、奥登的关系更亲密,矿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对性和地质很敏感,这些我都没有。
我所在的地区是幕阜山余脉的延伸部分,幕阜山在中国文化中很重要,是多个禅宗祖庭所在地,也是黄庭坚的江西诗派生活的地区。本地人都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农村老房子属于徽派建筑,我本人就住在徽派堂屋里长大。这些在我的诗中有所触及。我的叙述口吻、意象是自然发生的,虽然有一定的地域文化底蕴。
澎湃新闻: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理解您所说,“为了克服口语的单向和过分看重经验,我返回到知性和审美中”?意思是,经验要服从知性这个主体吗?
李建春:知性是能够选择和建构经验的,也就是说,你能获得什么经验其实也取决于你的意愿,包括爱。我不断地修正我的审美理想。前述的地域文化自觉,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发生的,作为艺术评论家,我做过不少当代艺术家的个案,他们一到国际上参展,就会遇到中国身份的问题。口语诗的问题似乎是:体制的内与外、日常经验、自由与个性等。当代诗人似乎应强调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当代艺术家只要是独立的个体,且有意思就行了。
澎湃新闻:1988年,您考入武汉大学,先就读于哲学系,后转专业到汉语言文学系。四年大学生活,您如何更进一步地爱文学?
李建春:有一点比较好:写诗很合法,这让我有一定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我读了卡夫卡、新小说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几乎全部翻译过来的西方戏剧家。那时候,现代派诗歌翻译过来的不多,但几乎全是精品。本科同学中,邱华栋、刘晖至今很活跃很重要,胡昉业已成为国际著名策展人,中文系插班生李浔也是名诗人。
澎湃新闻: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海子曾是您的引路人,您曾在海子逝世后不久去北京寻访他的踪迹,您也将自己的诗歌发蘖定在海子,而大约同一时期您写诗给海子,如《秋天的死亡》。现在您还认为海子以及他的辞世,对您的诗艺是一次开蒙吗?又或者说,您的诗艺另有来处?
李建春:海子给我带来的震撼,是他那赴死般的语言速度,强度,和规划。我那时似乎只能从海子的诗歌感受到汉语的血脉,而对其他社会性更强的他的前辈和同代诗人反而理解不了。我从海子那里学会了简洁,但也因为受了海子的影响,我写不下去。
由海子推荐的荷尔德林,翻译只有只言片语,里尔克的译文也罕见。学习这些西方诗人的劲头,现在想来,其实主要是被传记和评论激励起来的。要到我大学毕业多年后,我才慢慢收集齐必要的资料。我就这么成了一位诗人,很难说是因为读到了足够多的好作品,这很神奇。
澎湃新闻:早期,您有抄写誊录诗歌的经验,其实它象征着诗歌进入身体、进入生命。这件事的难度在哪里?在小资的、技术的今天,它变得容易了吗?
李建春:抄录诗歌的习惯是在大学里养成的,为了收集发表于杂志中的零散的现代诗。我发现,在自己写不了的时候,抄诗,因为书写的速度,能够模拟创作过程,虽然这是无限稀薄了的。我就是这样学习写诗。我曾把钱春绮译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完整抄了一遍。其他如弗罗斯特、曼德尔斯塔姆、里尔克、奥登、阿什贝利等,都是我抄的对象,即使有书了也抄。今天还有谁抄诗呢?
澎湃新闻:您是否修订了前期作品?我看有些作品比如《海洋是一种呼吸方式》非常整饬,深浅纵横辽阔而切己,似乎不像是一次性的成果。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您对早期阶段的珍视主要在哪里?
李建春:修订了。有的诗在不同的年头改过不止一次。《海洋是一种呼吸方式》倒是真的没改,这首诗曾被胡昉谱曲。语言整饬对我不是问题,关键是思想、经验不足造成的语义歧塞,改诗就是找到或止于“应有”的形式。
一个真正的诗人应在每一阶段都穷尽自己的可能性,推到被语言所伤的边缘。小诗人会受伤,大诗人不受伤。我大学毕业前后写得很多,修改发表的只是小部分,大量的习作要么丢了要么懒得改。你早期曾达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你后期能达到什么程度。此标准唯人自知。珍视?我并不珍视。我保留的早期诗是作为第一个路标。
澎湃新闻:1999年至今,您先后供职于《湖北美术学院学报(学院美术)》、湖北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好像您既离不开学校,又不太喜欢学校。学校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
李建春: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学会世故,而是维护和磨练自己的不合时宜。我其实能够舍的都舍了,之所以没离开单位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安宁的童年。我工作一直很负责,但也谈不上积极。
越是好的大学越是缺乏社会性。我虽然也在学院中,但社会性足够。这让我既是又不是学院诗人。我在湖北美术学院工作,先后作为编辑、教师,我在艺术、文化上视野开阔,但我不在文学行业,诗写得再好也不能积累地位。所以,我的工作其实很好。
澎湃新闻:1990年代是您在诗歌和履历上比较少提及的,在此期间,您大概在湖北之外做艺术和广告等相关工作,结交了众多诗友。总之,您似乎展现了与其他生命阶段全然不同的能量和活力。您如何总结这个阶段呢?
李建春:1990年代我在广州,像我这样的外来青年文化人很容易就相互认识了。我交往过的朋友,有些现在已淡出,著名音乐评论家和策划人张晓舟、艺术家大尾象工作组、王川、陈侗、黄专、郑国谷。真正在一起玩的有胡昉、凌越、连晗生、李凡。那时我很自负,远比现在自负。经常有过境广州的诗人相聚,陈东东、黄灿然、俞心樵、肖开愚……我与杨子是邻居,庞培为我找工作。还有女作家棉棉,做实业的有喻华峰夫妇。
1995年,我在太阳神公司(广东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时,出差乘飞机到重庆、成都、贵阳,拜访了诗人柏桦、钟鸣、翟永明、唐丹鸿、郑单衣。广州时期的活泼、自由、热爱、平等的气质,影响了我一生,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旦遇见阴沉的因素,总是默默地让开。
澎湃新闻:1995年您在成都会见柏桦,他提议您“要敏感”。当时您和同代的诗人交往多吗?他们又共享着什么价值观?
李建春:我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创作状态,多年下来,与当代诗人自然碰面、吃饭也不少了,但是深交的不多,比如2002年与马骅在武汉匆匆相会。我的生活条件不允许我除了买书、写诗、不上进之外,再为诗名而付出心力财谊。杜甫曾说过,诗人出名靠交游,我深表认同,没有人会为一个陌生人的优秀文本而激动得要如何。
澎湃新闻:今天很多年轻人的诗歌会呈现出疑惑、矛盾、情绪,等等,您的诗歌中很少有这些。是您可以避开这些吗?如果今天您刚二十出头,您会怎么写诗?
李建春:这个真的不好说。青春期欲望觉醒,有焦虑、痛苦,偏偏没有解决它的境界。这个时候最能显示一个人先天的本性是什么,你要不断地认识自己。中年以后你有或真或假的境界,但又善于在人性的矛盾中撒谎,通过诗能看出你是否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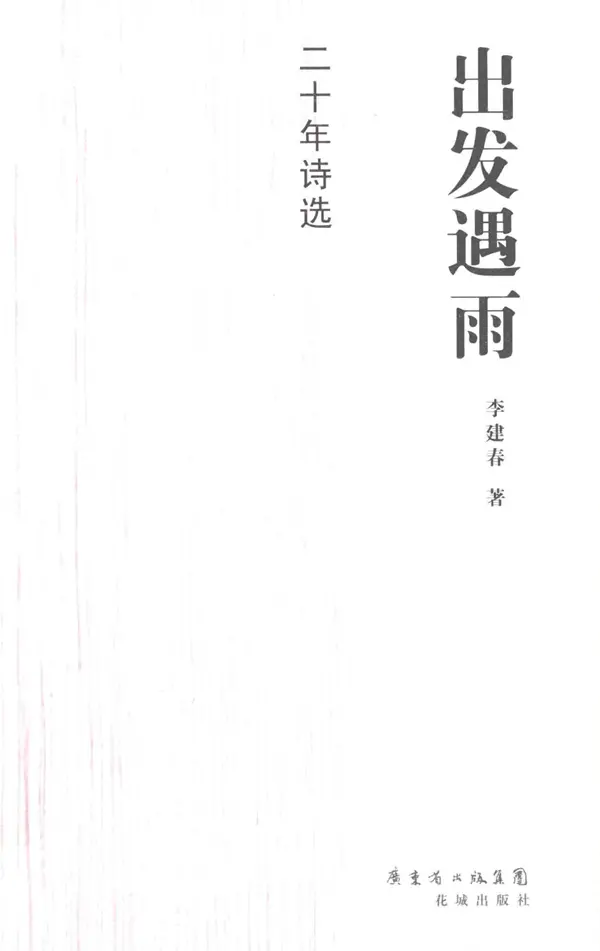
《出发遇雨:二十年诗选》,花城出版社,2012年7月版
诗神游历四十载
澎湃新闻:在诗艺锤炼期和精进期,您学习参考的现代诗范本是什么?主要是19世纪、20世纪欧美现代诗吗?在中国语境下,19世纪、20世纪欧美现代诗的缺憾或不适应是什么?在过程中,您在诗歌方面真的没有困惑吗?
李建春:译过来的都是在原语言中得到公认的大诗人。从译文虽然也可以读懂一个诗人,确定你喜爱与否,但不足以著文批评,这是我虽然读得很多,也深受影响,但没有评论过西方诗人的原因。你的问题是从整体上看。问题恰恰在于没有丝毫不适应,因此有缺憾的是我自己,如果我有王国维的眼光我就不会如此。
我曾说过风格本质上是一种道风,包括道风下的无道。我一介个体却被迫做着全体的工作,先是花了一二十年求道,并把道蕴压缩到语言里,成为道风(风格)。不过现在又有很大的不同,好像什么风都吹不进我了,这让我困惑不已。
澎湃新闻:1997年的诗作《钟面上的卧室》可以说是诗剧。你对诗剧、史诗等体裁的追求开始于哪里?您什么时候开始从抒情短诗走出来?或者说,您为什么将自己看作是长诗诗人?
李建春:我初中在镇新华书店买了三册本《神曲》,高中时读了不少浪漫主义诗选,大学时代读了我能找到的全部西方戏剧家作品,莎士比亚全集读了一大半,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全部译本。开局就是这样的,没办法。1997年我写了两个实验小诗剧,选本中保留了一个。关于现代诗只能是短诗的观点,经波德莱尔引用爱伦·坡之后,在英语中已成定说。但也有不甘的,比如法国诗人。爱伦·坡和波德莱尔的论述更使得长诗成为与短诗不同的东西。
古汉语诗词也只是短诗,屈原除外,而屈原有楚国的巫性,加上他信仰仙神,没有完全被《诗经》的传统同化。大约写长诗需要一定的宗教背景,我给自己加了一点。
澎湃新闻:大概以2000年代为界,您的诗歌分成了两个时期,前期语言疏朗,主客单纯且大小各持一端,后期语言凝重,主客往往互文,大小纽结。一前一后,浪漫主义变成存在主义,简体字标准语法变成语言炼金术。这个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李建春:你这个区分我很感兴趣。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50岁之后,即疫情之后,我又把之前的全部写作统称为前期了。关于你这个前后的划分,2000年我刚好30岁,也是工作到了湖北美院,稳定下来了。大学毕业之后30岁之前,由于生活动荡,在阅读上我是吃大学时代的老本,30岁之后我定下心来读书,自然会有些不一样。
澎湃新闻:2000年前,您的诗歌多关照物,如公共空间的物,如私人生活的物,如抽象与意象的物。诗人关照物比较常见,但一般还是以自己和主体为主,像您这样大面积关照物的情况几乎是孤例。后来你又如何“格”掉了物呢?
李建春:我很感激你认真读了我2000年之前的诗。但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不好回答。所谓言之有物,怎么会出现不关照物的写作呢。
澎湃新闻:您怎么概括或形容2000年代后的“悟道”“诗道”?或者如您所形容的真理的阶段、真理的形式阶段?又是什么导致了2010年代的丰收?
李建春:悟道与空性(道家叫无性)有关,涉及对待生活的决定性态度,孟子也谈过“不动心”。一神教的主体是神,神以莫测的意愿救人,人的主观性没用,所以不能称为悟道,可称为入道,即决定信仰一个特定的神,就像种痘一样,从此处处以此痘为原点,在心灵中楔入一个语言的楔子。2000至2012年左右我践行了西方主流宗教的真理,而由于我拒绝放弃人文立场,但又坚持信仰,所以我的写作是“真理的形式”,那十年是真正封闭的。2010年代我更成熟了,敢于把被宗教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
澎湃新闻:您的诗作有部分是以家为主体的,即家庭、家族、家国,当然它不只是一个群体概念,更是一个精神概念。不过近年可能有所变化。家为什么对您如此重要?
李建春:家庭是社会的基石,文明的依托。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诗人来说,家是语言减速装置。之后,又是调校价值观的标准。现在,该准备,或已经是晚期了,我又以家为精神流浪的肉身寄寓之地。
澎湃新闻:如今人们对传统的兴趣越来越少,传统也常常被拿来作为代用品、包装。在这种情况下,您思考传统的文化史和抽象精神,支撑点在哪里?
李建春:支撑点在于我始终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取其两端而折中,在此意义上,我是中庸的。
澎湃新闻:读您的诗歌,我特别感受到的是“中”,即比如说,地理的中、道义的中、文法的中。武汉是中国地理和文化的“中点”,它是中南大区的中心,也是区别于黄帝中心之外的另一个中心。如今之境,求“中”是否还有空间,是否还有完成的可能?
李建春:在格局上,是如上所述。中庸才是神秘的,极端才缺乏想象力。因此中是想象力的空间。圣人的领地是大众,大众最不可及。茨维塔耶娃赞叹里尔克的诗达到语言不可说的边界,根据我的观点其实还只是一端。
澎湃新闻:怎么理解您说的无我,无我和时代和众人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李建春:无我是汉语的品性,正如无时间。文言在语法上没有过去时和将来时,必要时增字表明,因此它实际上只有现在时,当下即永恒。也没有“自我”意义上的我、余、吾。但恰好是文言才写出了皇皇二十五史,有儒者继往开来的主体。因此你应把无我理解为汉语的品性与时代、众人的关系。
澎湃新闻:怎么理解您说的“疫后诗学”?
李建春:疫情开始后我就预感到一个不同的时代来临。当时我谈到疫后诗学是因为我看到一些东西,意识到简单的说真话已是崇高和神圣。大流行的三年来,我也尽力地见证了,体验到见证的苦涩、无味。作为武汉人,我意识到我站在全球最有资格见证疫情的位置。这个工作已差不多完成,我是真的受伤了,陷入某种精神紊乱。
澎湃新闻:如何抢救我们的语言和文化?
李建春:元末的乱世气,产生了狂草和伟大的文人画。明末仍然是狂草,产生了董其昌的摹古和顾炎武、黄宗羲等,连君权都敢否定。或许“抢救语言和文化”相当于董其昌的摹古吧。这又回到前述的同时承担“自由和中国文化”,但也许,什么都不承担只承担自己的“狂草”才是一切。而董其昌的摹古,是追摹古人的笔墨精神构造一个自足的语言世界,身处乱世而逆向地寻求一种清淡的味道,他笔下的山水,不再源于实际的造化,而是一个如万古般寂静的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