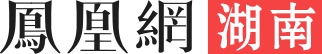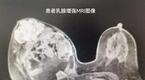张草原:在我二十九岁这年,我发现我比我外婆高了


独家抢先看
下河捞鱼捉虾,或上山摘野果、拔草药,在村子里面长大的孩子们,与天地间的距离无比接近,所有的童年游戏,都伴着乡野的风、山间的虫名鸟叫……而当我们成年之后,只能靠短视频里的李子柒或者华农兄弟来重返当年的记忆。
在下文作者张草原的笔下,每个文字都在回忆里跳动,组成一段段我们向往着的旧时生活——赶大集、看电影、上山下河、抓虾喂鸡。文字中干净、纯粹地再现了一个南方小村庄朴素而简单的生活,也勾勒出了长大后的我们向往的生活。
本文摘选自《你好,小村庄》,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赶大集
在我二十九岁这年,我发现我比我外婆高了。
外婆体形高大,走路时身子有点儿左右摇,远远地走过来,像只慢吞吞的熊。
小时候我最爱去的就是外婆家。
妈妈开始学做生意。外婆赶集常到妈妈的档口,拉起坐在地板上正把蟑螂的翅膀卸掉的穿着粉红色蓬蓬裙的我,要带我一起回家。妈妈总是不答应,因为外婆有大把农活儿要干,不忍增加她的劳累。外婆不高兴,板着脸,噘起嘴巴,像个受委屈闹脾气的老小孩儿,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板着脸,噘起嘴巴,趁妈妈还没反应过来,手给外婆,外婆牵着我就走,妈妈连忙追上,快速塞点儿钱在我口袋里,带着警告的语气说:“不要闹阿婆买东西吃啊。”

时候不早啦,街上赴圩(集市)的人散了一大半,街上的酒摊儿也准备收桌。
庄稼有季节,耽误不得。靠土地营生的人,脚扎根在泥土里,即使离开田地,洗净脚上的泥土,脚步也迈不轻松,他们把四季背在了身上。
会酿酒的女人挑上自家酿的酒,在街上支一张小桌,再摆几张小塑料凳,放一叠碗。一碗淡黄色的水酒两毛钱,一碗红赤的娘酒也是两毛钱,好酒的人坐在一起,随便聊上一句,一碗碗酒下了肚。冬天的酒香最馋人,一碗下肚,全身都暖。水好,土好,酒就多。街上的酒厂开窖时,不用春风相送,闻着闻着都醉了。酒鬼也多,一条街,这里躺一个,那里躺一个,呼噜声四起,一个比一个响,好似较劲地比着谁肚子里的酒最香。
外婆把我带到肉丸店,笑着说:“吃了肉丸回家可得自己走路哦。”肉丸店老板娘守在灶台前,脸又圆又红润,常年用一对红色的塑料发夹把刘海分两拨夹住,像个大胖娃娃。老板在挖肉丸,一盆打成糊状的肉糜,一盆水,左手抓一把肉糜,轻轻一握,一颗圆圆的肉丸从虎口处冒了出来,右手的调羹把肉丸挖了放水里,一起煮熟。一块钱一碗肉丸汤,撒葱花和胡椒。先嘬一口汤,汤的香甜和胡椒的辛辣冲刷着唇齿。一颗肉丸把嘴巴塞得满满当当,外婆看着笑,接着帮我吹凉下一颗。
我当然不会自己走路回家,还没有走多远就喊累,外婆蹲下把背留给我,我跳了上去。
走在国道,两边水田秧苗刚插,燕子斜飞剪过水田,外婆摇了摇背上的我:“你看,燕子穿花衣飞回来了,你也是燕子。”
我把脸贴在外婆背上,湿湿的。外婆容易出汗,但汗味儿不大,混着衣服上的肥皂味儿很好闻。听着外婆说话,看着时不时超过我们的自行车,认识的人会按铃打声招呼,外婆看着背影大声问:“你也赴圩?”“系(是啊)!”骑自行车的人回头匆忙应答后继续赶路。羡慕着会骑自行车的人,无心回答外婆的话。

到了村子,野蔷薇,白的,粉的,红的,这里一大挂,那里一大挂,我要外婆停下,伸长手去摘花,外婆头上戴一朵,我戴一朵。在田里干活儿的人都认识外婆,路过时起腰打招呼:“这是你三嫲(三妹)的女儿?都好大了。”“系!嘴巴像极了我三嫲。”外婆答完,哈哈大笑。
一条一米宽的田间小道连着大路和外婆家,路口有墩竹子,又浓又翠。到了这里我要求自己走,刚下地就跑。家门口是一片水田,这一片平坦广阔的土地像布,秧苗绿时一片绿;水稻黄时一片黄。我一边跑一边对着远处的山大喊“啊”,山也不会把我的“啊”客气地还回我一点儿,我才不想要。花掉了我才回了一下头。
外婆的话真多,关于妈妈,关于爸爸,关于妈妈和爸爸。回家的路很长,我趴在外婆的背上也不觉得远。
我说她:“你把我妈宠坏啦,她总是发脾气。”她说:“你妈不也这样宠你?”
跟妈妈生气时最常说:“我去阿婆家住不回来了。”妈妈一脸鄙夷:“你去啊,自己去,那么远看你自己能不能去。”
哼,我才不觉得远。
跑到家,快速从屋檐下取下簸箕去水塘里捞鱼。水塘就在家边上,我一拿簸箕,外婆养的猫立马跟着我。外婆呢?去给我弄好吃的去了。
看电影
我有一条公主裙,粉红色,正中绣着一颗桃子,裙摆有三层。我穿着这裙子出去,遇到认识的人,总要展示下裙子的厉害之处:“它有三层,你看,我的裙子很厉害。”说完,我还一层层地掀开展示给眼前的人看。
“好厉害。”
获得肯定后,我旋转起来,裙摆飞起时,我像只要飞的蝴蝶。所以,当外公说晚上坪上有电影看时,我当然要穿我的公主裙去。

吃晚饭时外公说:“快点儿吃,不然去晚了电影都开始了。”
我立马张大嘴巴,把饭往嘴巴里扒,饭扒得多了,一边嚼饭粒一边往下掉,安安立马过来舔了个干净。安安是外婆养的土狗,每次去外婆家的第一天,刚到院子,安安都要冲我吠几声,被外婆呵斥后才安静下来。相处了两天,安安就知道我每次吃不下的饭都会倒给它,还有那带肉的骨头,趁外公、外婆不注意时我也会偷丢几块儿给它。一到吃饭时间,安安就守在我位置的桌底下,咧开嘴,眼巴巴地望着我。为了早点儿去看电影,我扒一口饭,再扒大半给安安。
好不容易把饭吃完了,外公又拉着我说要给我扎头发。
外公那双手,粗笨有力,张开手掌可以把我的头顶全部罩住,我的头发稀疏细黄,上一次他帮我扎头发把我的头皮扯得又痛又麻。外公看我迟疑,说:“穿着裙子要扎头发才更漂亮啊。”看外公手里已经拿好一把红色的小塑料梳子和一根黑色的橡皮筋,我只好硬着头皮让他扎头发。
坪上是一块儿大水泥地,是村民平时开会的地方,水稻收割完,放映队下乡,用电影来犒劳村民仲夏经历的每一场火热。
等到我和外公出发时天已经黑了。外公把我放在他肩膀上,我手抱着他的头,外公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长烟斗。小路两边没有路灯,溶溶的月光从天倾泻,就着月光,外公把走了成千上万的小路踩得踏实有力。山谷里夜鸣的鸟儿把夜叫得空旷又深寂。远处人家亮着昏黄的灯,有些人家过年在门口挂有灯笼,这天也会特意点亮,漆黑的夜,红的灯笼,像从沉睡中醒来的怪兽的猩红的眼。
我觉得害怕,用力箍紧外公的头。外公说:“别怕,天上有那么多星星。”
抬头看天,密密麻麻的星星如水泼地溅起的水珠,蹦了上天,成片。我们在走,无穷辽阔的天际也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乱了步子,跟着默默移动。

快到坪上时,遇到的村邻多了起来。小孩子在前面快步走,大人腿虽长,但习惯了在泥土地里的挣扎,步子迈得并不开,都被孩子们甩在了身后,小男孩儿剃短的头发,像收割后稻田里剩下的一茬儿茬儿稻梗。小孩儿遇到了玩伴,大家追逐满场跑,大人的叫唤和叮嘱根本不管用,如果不是悬空拉出的幕布上亮了光,我相信他们一定能追逐到天亮,光让他们安静下来。
电影开始了,迎着幕布上的光,大家把板凳放下坐了下来,外公没有带凳子,站在最后面;而我在外公的肩膀上不愿下来。跟外公站在一起的是上屋的表舅,表舅镶了几颗金牙,一说话,闪着光。他掏出香烟,是青梅软装,绿色的,递给外公一支,村里的男人一见面就掏烟,各自点上烟后,用力地吸一口,吐出,再说话。外公带着长烟斗,兜里只有烟丝,抽完表舅递的烟后掏出自己的烟丝,扯出一点儿,装进烟斗。外公抽的烟,往上升,烟飘散在我眼前,把电影整得云里雾里的。
比电影吸引人的是前面那个坐着的剪着齐耳短发的女人,嗑着葵花子儿,放一粒在嘴巴里,“咯嘣”地咬破壳,用舌头卷出子儿,把壳吐地上。再往前点儿,那个胖胖的穿着无袖碎花上衣的阿姨从家里带了袋水煮花生,外婆家的花生也都挖完了,挑小个儿、不够饱满的用盐水煮,胖阿姨的花生应该跟外婆种的花生一样的香甜吧?村尾的村民骑着摩托车来,村里有摩托车的人不多,尤其是像他这种的红色大嘉陵更少见,他靠在摩托车上,不看电影,跟身边的人交谈起来,时不时看着场内的村民,有正好认识又看着他的,他立马招招手。比我还不认真的就是村民带来的狗了,这狗汪一下,那狗汪一下,附近没有跟着来的狗也不停“汪汪汪”地回应着。
电影结束了,白色的幕布灯暗了,坪上也暗了。

比我还不舍得回家的是村民,开始跟周围的人聊了起来,一句电影,两句庄稼。电影放着时,大家都没觉察出坪上蚊子多;电影放完了,村民的手挥个不停。
聊天也是外公爱的,跟村民聊酒,聊焖肉。大家走完,外公才背着我回家。
热闹喧哗的坪上瞬间安静下来,草丛里的鸣虫“吱吱唧唧”地叫着,此起彼伏。天上的星,地上的虫鸣,送着埋头回家的人。
到了家,外婆已经睡下了,门口亮了盏灯。外公打着手电筒直接把我放到外婆床上,外婆拿着蒲扇的手搭放在额前,闭着眼睛。
我爬了进去,外婆的床结实稳固,晃都不晃一下。外公出去了,房间一片漆黑,不用灯我已经知道枕头边放有一颗苹果,我闻到了苹果特有的清香。外婆拿着蒲扇的手又摇了起来,蒲扇的风又轻又凉,她没有睡,问我:“电影好看吗?”“好看。”“讲的是什么?”“不知道哦。”
“把苹果吃了睡吧。”也不知道外婆把苹果放在哪里,每个晚上关了灯后总会摸出一个苹果给我,我快快地把苹果吃完,汁儿弄脏了手。把核递给外婆,外婆伸手把核放到床边的梳妆台上。手上残留的汁儿黏糊糊的,在身上擦了擦,裙子挺括的手感让我猛然想起今晚我居然忘记给大家展示我裙子的厉害之处了。
电影的夜,有光;幕布暗了,今夜村民的梦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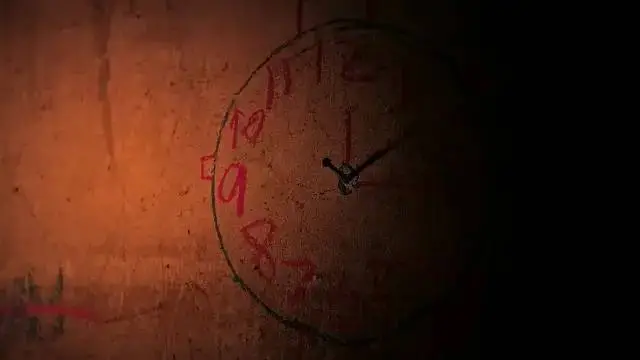
下河捞鱼
妈妈把头发扎成一束马尾,刘海丝薄盖住额头,穿着的确良紫色底碎花短袖衬衫,齐膝盖的短裤,光脚,拿着簸箕,拎着塑料小桶出门,站在院子东南边的芭蕉树下叫我:“野猪,走,带你去河里捞鱼。”往日里妈妈总会厉声交代我,不可以一个人偷偷去河里捞鱼。而今天妈妈站在翠绿薄亮的芭蕉树下居然主动叫我去河里捞鱼,别的不敢夸,捞鱼我可比妈妈厉害。
河两米宽,浅水,河沙干净,夏日的阳光投放到河里,被河水漾出一段段波光,似星闪耀。我和妈妈双脚踏进河里,河水清凉,把脚上发烫的暑热卷走,我们搅翻河泥,水波动荡,在河中晒着太阳的螃蟹察觉出异常立马横着冲进河边的石头缝里。若平时,我会把石头翻开,躲在石头下面的螃蟹可不止一个。妈妈让我拎着小桶,她来捞鱼。
妈妈把簸箕对准河边的阴凉处,那里水深些,靠岸边,鱼藏得多,脚伸进深处一阵乱搅,再快速地提起簸箕,簸箕底翻腾着小鱼儿,有扁扁的银白肚皮的小鱼,也有身披彩衣的鳑鲏,还有蹦弹着的虾米,螃蟹速度最快,簸箕刚提起,螃蟹横冲出簸箕“咚”地掉回水里,迅速躲进长满绿色苔藓的石头缝里。
红桶装些水,小鱼、小虾装了进去,妈妈在前领着我一直往上游走。一个人来河里捞鱼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一直走,往前走会有大而光滑的石头,太阳被肆意生长的野蔷薇挡住,四五月野蔷薇开了,粉红的,纯白的,交叉生长,风一吹来,河里花香涌动,躺在大石头上,看着花瓣唰唰掉下来,数不清是白的多还是粉的多。现在,仲夏的太阳,从叶间漏下来,砸在暗黄光滑的石头上,像一块块碎银片,手一拢,叮铃铛啷的。

走到上游的梧桐树下,小桶里的鱼已经有不少,妈妈看了看说:“嗯,有五六斤的样子了。”妈妈把簸箕上挂着的草拨弄掉,洗净小腿肚上的淤泥。妈妈站直,目光顺着上游走,继续往前,就是山了,河水是从山上下来的。妈妈说:“我们泥坑子这条河啊,可是很特别的,别的地方水往东流,而我们这条河的水是往北流的。”她唇齿之间迸发出的字词语句中带着某种自豪。这样的话,去年秋天妈妈带我来河里洗芭蕉芋粉时就说过。用一个大陶盆,盆内沟沟壑壑,地里挖好洗净刮去根须的芭蕉芋在盆内的沟沟壑壑上来回擦,脆嫩的芭蕉芋在粗糙里伤了心,在盆里摊烂成泥。一箩筐擦好的芭蕉芋浆挑到河里洗粉,用网布盛浆,让河水冲洗出浆,她一边洗一边说:“这河里的水啊,就是泉水,洗过的芭蕉芋粉都是甜的。”我说:“嗯?你之前不是说芭蕉芋粉甜是因为种它的泥好?”
芭蕉芋种在祖屋院子前的菜地里,泥土乌亮,平时在院子里洗菜淘米,水通通泼到芭蕉芋下,鸡、鸭在院子里屁股一撅就拉屎,扫把一推,也到了芭蕉芋地里。好几次母鸡下蛋少了,妈妈拿着锄头在芭蕉芋地里挖一挖,又红又长的蚯蚓交叉爬行,母鸡使出护崽的劲儿,气势汹汹地不让别的鸡、鸭靠近。
妈妈把小鱼、小虾倒进盆里冲干净,用手挤掉小鱼的肚皮,在院子里觅食的鸡都跑到天井,妈妈让我负责赶鸡,鸡一心想啄鱼、虾,被我一赶,胡乱窜,天井正中的朱顶红盛开着,翠绿的花茎,鲜红的喇叭状花朵,像美艳起舞的仙子,而鸡一点儿也不爱惜,蹿到朱顶红上,尖利的爪把长长的叶划伤,还差点儿把花茎给撞断了。我从地上捡起扫把,把鸡拦住统统赶到院子里去,而妈妈把鱼、虾收拾干净了,她正从橱柜的最上层取下去年秋天晒好的芭蕉芋粉。妈妈爱惜这些粉,一年才洗晒出十几斤的粉,日常家里炸肉、炸鱼少不了它,妈妈怕我跟之前一样把整袋芭蕉芋粉用来当糯米粉做粄玩掉了,放在橱柜最上面,让我垫着凳子都够不到。芭蕉芋粉撒在鱼、虾上,撒盐、撒姜丝和葱粒,裹匀后,起油锅炸。
一直躲在屋后树林里看书的哥哥顺着烟囱里散出的香味儿回到了家,书还没有放下,直接进厨房,拿起一条刚炸好的小鱼就吃。小鱼刚起锅,还烫,哥哥龇牙咧嘴地咬几下吞了,我刚吃完几条小鱼,看到哥哥吃得这样着急,忍不住又想吃,手伸过去,被妈妈拍掉,说:“你已经吃了不少了,等会喉咙痛了。”转头看着哥哥吃得猴急的样子交代他:
“你也别吃多了,刚起锅很热的。”
不让吃了那我就出去玩儿吧,省得待在厨房里闻着香又吃不着。走出厨房,凉爽的风吹来,脸上的汗滑下,痒痒的。出门去院子里摘薄荷叶,薄荷随意种、随意拔,下几场雨又疯了般长,只要有泥土,不分贵贱地热烈活着。捏碎薄荷叶,放鼻前闻闻清凉醒脑,擦在脸上,风轻轻地吹着,冰冰凉凉,舒服极了。院子里还有酸酸草,摘掉叶子,擦擦根茎放嘴巴嚼,酸酸的,炸鱼的油腻被遮掉了,只剩下草的酸和鱼的甜。妈妈说芭蕉芋是甜的,我没有尝出来,但是我知道芭蕉芋的花像喇叭,摘下来从根部吸,有蜜。转过头,看到祖屋院子前的芭蕉芋顶着一朵朵鲜红的花,把身后的墨绿山谷点亮,调头去祖屋摘花吸蜜。

吃饭的时候,我和哥哥都不甘示弱地一筷子、一筷子地夹鱼、夹虾米,妈妈没有再提热气的事儿,任我们吃。天井的水缸里泡着一个大西瓜,是早上妈妈去菜地摘回来的,一刀落下去,西瓜爆开,清甜的汁液流出。清甜多汁的西瓜正好抚顺仲夏的闷热和油锅里翻翻腾腾的煎炸。
我和哥哥撑得肚子似装了大西瓜,两个人站在门口望着远处的山,听着屋后风吹竹林沙沙,想着妈妈什么时候再来一盘这样的鱼、虾。这样香脆鲜甜的鱼、虾是泥坑子的秋风和夏水滋养出来的,被妈妈炸成了一盘。家在一盘盘的秋风和夏水里落下了胃。
摘野果、拔草药
爷爷的爷爷,为了讨生活,选中了一个山之外还是山的地方扎根,这个地方叫泥坑子。开山破土,在半山腰上建房子,开梯田,挖水塘,锄菜地。从我记事起,泥坑子就住了那么三四户人家,不是叔公就是大伯、叔叔,开始大家住一个祖屋,后来各自在祖屋旁边建了泥砖黑瓦的房子。泥砖是自己弄的,上山挖黄黏土,混着沙子和稻草加水搅匀倒到砖模里,压实,脱模,晒干。没有人跟我玩儿时,我自己跑去后山,摘果实,拔草药。
泥坑子有不少老果树,据爸爸说,这些果树是爷爷还小时就种下的,分布在去梯田的半山腰上、山谷下的菜地边儿和屋后的树林里。我午睡后头昏昏沉沉的,穿上红色塑料拖鞋,走到衣柜里,翻开小时候穿过的棉衣、棉裤,找出前些日子藏进去的李子。哥哥爬上长满青苔的李子树,摘了往下丢,我捧着斗笠捡起放进去,哥哥不担心我偷吃完,刚摘的李子又青又涩,端回家,放墙角,过段日子才能红。我嫌慢,往衣柜里藏。熟了的李子又红又软,散发出阵阵馨香,一口咬下去,汁液往下流,李子的香甜布满味蕾,把午睡后的昏沉寡淡冲了去。
吃不够。顶着滚烫的太阳翻到后山。后山有棵大的沙果子树,一粒粒黑黑的如小拇指盖儿大的沙果子摘一把丢进嘴里,酸酸甜甜的,山上的风吹过来,整个人凉爽、清透极了,真想就地打滚儿,从山的这头儿滚到那头儿,再滚回来。最酸的要数“鸡合子”,形如腰果,小小粒,熟时淡黄,皮薄,有仁,摘一粒放嘴巴里,用舌头卷住吸,酸得我,不停地咽下口水。
经过树林时,抬头看到一棵青青的果实挂在树上,捡起树棍敲下来才发现是李子,看那树,老皮表面疙疙瘩瘩,至少有二十几年的树龄了,长得瘦直,隐在毛竹和杂树丛里,若不是无意发现了这颗果实,任谁也不会知道那里长着棵李子树。找了找,发现这李子树只结了一棵李子,仿佛是用积攒了年年岁岁的力气才结出的这么一颗果实,想了想,觉得这颗李子尤为珍贵,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果实吧?把李子仔仔细细地吃了,爽甜清脆,再诚心诚意地许个愿:赐我长生不老吧。

吃够了果子,拔草药。基本的草药都是奶奶教认的。喉咙红肿,偶尔发烧时,奶奶就从路边拔些一包针和色麻头,剁下根块,用水洗净黄泥,熬出一碗水让我喝下。伤了风寒,就从田埂处找些鹅不食草,蒸热,从房间衣橱里找出个银戒指跟鹅不食草一起用纱布包着,往我额头,后颈匀匀用力揉着,只觉得身上热乎乎的,痛如千斤重的头也慢慢化了开。白亮的银戒指变得蓝黑。奶奶说:“你看,你受了恶风。”奶奶也从山上砍些枫树回来,从屋前砍几枝桃叶,洗干净煮一大锅洗澡水,趁热搓洗,洗得一身通红,裹着长外套,躲进被窝,出一身汗,睡一觉,醒来病就好了。而家里最常煲的是凉茶。
靠河、靠溪的地方就有狗贴耳,背阳的山坡上多三菱棍,还有贴着地面的车前子,摘一大把回家,洗干净放院子里晾晾,傍晚妈妈就拿来煲凉茶。夏日的傍晚,暑热还没有完全退去,站院子里还有酷夏的余温甩到脚上,风开始凉了,院子里烧着布惊树和艾草驱蚊,一壶凉茶放桌子上,吃完晚饭、洗完澡的一家人坐在竹椅上,脚搭在桌上,喝碗凉茶,淡淡的药草香混着洗不掉的泥土腥味儿,把夏季的燥热缓缓冲掉,看着山那头的天空慢慢变暗,直到完全变黑才回屋。
没有野果摘且不拔草药的时候就去看坟,一排排的旧坟就安在去番薯地常经过的路上,整整齐齐,水泥发黑,日晒雨淋,有个别坟墓出现了裂痕,坟前长满杂草,墓碑上有字,不认识,但是知道这一排排的坟墓里面安葬的都是自家祖上的人,不害怕,给坟前的每个杯子装满泉水,说一些话:看到了一只野兔,没有捉住,不知道野兔怎么来的;在祖屋的墙根下发现了几条红色杂纹的蛇,晚上会不会来咬人?晚上有“坏鬼”来了,不给开门,会不会从天井那里飞进来?
长大后离开老家十多年,可当再次踏上老家的土地,心里清清楚楚:回家了。我的根在这里,我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若有一天老去,我一定要回到这片土地上,跟这片土地融合在一起,再也不远行。

本文选自

《你好,小村庄》
作者:张草原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鲤伴文化
出版年:2022-4-30
编辑 | XuYan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 | 《路边野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