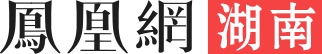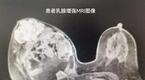何立伟:当时院子当时人


独家抢先看
作者:何立伟,作家,生于1954年,长沙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长沙市文联名誉主席、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其小说代表作《白色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收入人教版中学教材。出版有《小城无故事》、《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亲爱的日子》、《白色鸟》等二十余部小说、散文集。获各种文学奖励二十余种,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译介到国外,被评为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一百位中国作家之一。
除开小说创作,还从事绘画与摄影创作。在旧金山及北京上海等地举办画展和摄影展,作品成为许多刊物封面和作家新书插图,深受观众与藏家喜爱。
中央电视台曾拍摄上下两集纪录片记叙何立伟在长沙的生活,以此成为长沙文化的代表人物。
长沙1938年的“文夕大火”,致三万余人丧生,更惨的是,全长沙城90%的房屋付之一炬,俱为焦炭,让人无家可归,成为流民。于是文夕大火在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三大惨案。
虽然之后长沙城一砖一瓦重建,我们也只能从发黄的老照片上看到1938年之前老长沙的模样了。
那些老照片中,最让我着迷的就是一些带花园假山回廊曲拱的深宅大院,贵气、雅致、幽静、怡心,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乃是作为文化名城的长沙在宅住上的华丽代表,也是古城官府与民间相生相成的世俗栖居文化的可视的载体。
当然38年之后建起来的长沙的屋舍,也是民国风的屋舍,尤其其中的宅院,住着殷实人家,日子亦是过得细水长流,可惜经过最近三十年来拆旧立新的大规模城建改造,如今已是所剩无多了。这些宅院砖石上的青苔苍茸,仍斑斑点点地显示着岁月同沧桑,显示着时间深处的流年与或静或闹的长日。
或许是某种不可知的因缘或命定,我的成长经历及日后的工作,差不多总与这些长沙深街小巷里的深宅大院有瓜葛牵绊,于是便有无尽的回忆。
我出生的地方是长沙老城的一条僻静小巷甫觉里,小巷夜阑里只听得偶尔有人过身,橐橐的就是他的鞋跟声递到枕边来,像深庙中轻敲的木鱼。甫觉里有几栋民国老公馆,我的出生地就在其中的一栋,据说从前住的是国民党军的一位师长。大门漆黑,悬着铜门环,门环扣响时,大门左侧一扇小门便打开来,进去是不算太大的一个带天井的院子。两层楼的公馆,楼下的大厅极是轩敞。大厅两侧各两间房,楼上的格局与楼下同。厅大,房间亦不小。皆是木楼板,雕窗,四五米的层高,通透中揖让着满室岁月的光亮。
49年师长逃到台湾后,这栋公馆当然地就充了公,住进来四户市政府的干部。我家住的是二楼东向的两间房,对面西向是财政局的蒲姓干部,有一个比我大三个月的崽,也就是我的发小。我们一同进的幼儿园,又一同进的小学。楼下两户中有一户姓焦的,两口子年过半百,无后嗣,多闲暇,于是移情花草,在院子里种了美人蕉同枇杷树还有夹竹桃,天井四围亦种了兰草。
好看的当然是美人蕉。美人蕉在北方花期只有夏秋两季,在南方,则全年开放。当然最盛亦是夏秋两季,红得呵就像元稹在《行宫》诗里形容的“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那种红确是让人红得有情绪又有心事的。焦姓太太留着那个年代女干部的短发,穿着灰色的列宁装,总是在院子里浇花,手里提着一把铝皮的喷水壶,模样专注,眼神痴呆。我后来才听得大人讲,焦太太有一年夏天过生日,在其时古城最有名的长沙饭店庆生,头顶天花板上吊风扇忽然掉下来,飞旋的扇叶削开了她脑壳的天灵盖,抢救后留下后遗症,渐渐眼神变得迷离。但她爱干净,列宁装总是熨熨贴贴,短发亦一丝不苟。又尤其勤快料理花事,下班回来就提铝皮喷壶给花花草草浇水。浇完了,抽把竹凳坐在庭中,呆坐如一尊木菩萨,而满庭花草则生机怒发。美人蕉红得让人感伤。据说焦太太从前是个美人。但我们不大看得出,亦想象不出。
念小学之后我搬到藩后街七号大院,里头住的统是市政府各机关的干部,大约有十来家。大门里头进去前后两进,各带一个两三亩地大的庭院,两栋有大理石罗马柱带半圆形阳台的比较西式的砖楼,亦都是两层,另有一长排平层厢房,地上铺的是灰色方砖。庭院四周拿红砖斜斜地埋成锯齿形围了一大圈。我们细伢崽常常就在锯齿上张开双臂飞奔。而细妹子则在庭院里跳橡皮筋或者踢毽子,亦都锐声叫唤,快活无比。七号大院有二三十个小孩子,一放学,院子里就热闹起来。除前述各种把戏外,又还有打弹子、砸金花、打游击、玩跪碑、放风筝、滚铁环、丢手绢等等无尽名堂。总之弄得整个院子鸡飞狗跳。而大人们呢,则在家里择菜做饭,于是家家户户飘出了饭菜的香味,蓝濛濛的烟子在院子里如薄云浮荡。过后,就听得各家大人朝门外头喊:细毛,大毛,三毛,红妹子,狗伢子…….回来呷饭!
吃完了饭,或者月亮就浮出来了。前院罗马柱挑起的半圆阳台上,姓蒋的同学的妈妈就开始拉二胡,洪湖水呀浪打浪,或者,二泉映月。小孩子们这时就在灯下做作业。细伢崽做完了,就溜出家门在院子里玩官兵捉强盗。“强盗”躲在罗马柱后,朝“官兵”喊:来呀,来捉我呵!于是只听见院子里都是没方向的鞋跟响。
这就是我们童年的生活,小孩子们在大院无忌的友谊中一起长大,四季的风一吹,个头就窜到了一米六。
在藩后街同一条街,我家后来还搬到了四十七号院子。这院子是三进,前一栋是两层高的小楼,中间同后面的一栋则皆是平房。有两个大坪。这院子住了六户人家,亦都是市政府的干部。前坪里左右各有一棵好大的梧桐树。阔大的树叶伸到了二楼人家的窗户里,有风吹来则飒飒如耳语。这院子里有六个细伢崽,两个细妹子。妹子都是爱学习的,成天抱了书在家里头看,嘴里含着咸味奶糖,藕尖样的小手指在书页上一行行划来划去。伢崽则成天翻墙,坐到大门顶上的屋檐上,拿弹弓射停在门前苦楝树上的麻雀。或者跳到院子外民居伞形黑瓦屋顶一线红砖上踮脚飞奔如同“三侠五义”里头有轻功的好汉。我们自已动手做弹子盘车,就是搓衣板大小的木板上装四个大轴承,前面的两个轴承是装在方向盘下,做好了就拿到大门对街菜市场好大的一块水泥斜坡上去玩,一个人坐着把控方向,一个人在后头推,推出速度了,就双脚踩到弹子盘车的后头,扶着前坐人的肩,哗哗响着朝前滑去,两耳生风。有时候两台弹子盘车互相对撞,撞出尖叫同笑骂,人仰马翻,摊在水泥的斜坡上。于是看见幼儿园窗玻璃一样蓝的天,同天上慢慢移动的白云。
我们还在前坪上装了副单杠,就是拿从浏正街上一家街办工厂里偷来的一截两米长的空心钢管,在院墙上凿一个洞眼,把钢管一头插进去,另一头绑在梧桐树上固定。院子里伢崽们每天早上便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或者叫人帮着做大回环。做大回环时经常有人摔下来,跌得鼻青脸肿,先是哭,然后笑,骂不晓得是谁的人家的爹娘。
何解要练单杠?是因为要增长臂力。何解要增长臂力?是因为我们院子里的伢崽经常同街上的伢崽打群架。其实那种群架打出的是一种热闹,像是互相起哄,并无什么伤亡。过程中口舌的用力远胜拳脚。
夏天里,我们就打着赤脚,踩着麻石路——那时节长沙的老街巷都是铺着麻石的,穿过解放路,穿过东牌楼,然后西牌楼,然后太平街,跑到湘江边上游泳。站在趸船上,排着队朝河里头跳,双手贴股,眼一闭,腮一鼓,笔直地朝下头跳。我们把这样的动作叫做“丢炸弹”。我们在河里头打水仗,溅起浪花无数。麓山像一头卧牛,伏在河对岸静静看我们不要命的嬉闹。河里头船上的白帆像日历纸一样一页一页翻过去。时间也当然地翻了过去。
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坐在屋顶上吹牛皮,海阔天空地吹,无涯无际地吹,吹过了就迅速忘却,第二日又接着吹,其实说的统是前一日说过的话,又绝不觉得是重复。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家又搬了一次,搬到了东庆街芋园里。也是一个院子,中间一栋两层楼,环着它四周是平房,前后各两个天井。这是普通民居的院子,住的十来户也是普通的人家,有教师、泥水匠、裁缝、工人。院子大门外有一口井,井壁上长满了凤尾草和铜钱草,井很深,井水离地面大约有三四米。院子里的人都在这口井里打水,煮饭洗衣也都是用这井里的水。井口冒出森森的阴凉气,所以街上三伏天夜里就有人把竹床架在井上困觉,连莆扇都不用摇。而院子里细伢崽细妹子则把竹床架在有青苔的天井里,听大人讲鬼故事,被屋檐围住的四四方方的夜天里,闪动着繁密的星光。
我跟泥水匠的两个崽玩得好。他们的娘已不在了,爹在建筑工地干活,每天下班就夹一捆工地上拣的柴禾回来,所以只有他家里是烧柴火饭。锅盖揭开来,满院子都是饭香。他家里四壁,包括一年四季都挂着的蚊帐,亦都被柴烟薰得墨黑。
两个崽的成绩都不好,又调皮,时常旷课,老师上门告完状后,爹拣起地上的柴棍劈头盖脸一顿乱扑,然后把扑得一头开坼的柴棍一丢,坐在有蚊帐的床上抽喇叭筒烟。整个过程不说一句话。这时节每每邻居就拢来劝他。他也只抽烟,不说话,眼前翻卷着一团一团灰蓝的迷雾。院子里当教师的姓周,是个女的,就对停止了哭喊的两个崽说,你们做作业,有搞不懂的地方,就来问我。听话,要按时做作业,千万不要旷课。两个崽一脸茫然,好像周老师是同别人在说话。
其实这两个崽只是不爱上学,其他的事情,院子里别人家的细伢崽没有人能比,譬如上树摘桑叶,譬如做木头手枪,譬如打井水——打井水还真是要技术。我初初打水,桶子在井里晃来荡去,就是飘在上面舀不上水。他家老二上来,抓住桶绳,轻轻一带,桶子就低下头去咕咚咕咚饮满了水,三把两把提了上来,“给”!
我们在院子里玩官兵捉强盗,他兄弟当“强盗”,我们就是捉不到。他们要么爬到天井的玉兰树上,要么爬到人家阁楼夹板里,总之就是捉不到手。
我后来搬离这个院子,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两兄弟。他们时常在柴火堆里煨了红薯,脏兮兮的手翻来翻去地捧递给我吃。有回还烤了大蚱蜢给我吃。他们对我真好。
兄弟俩老大比我大一岁,老二同我一样大。我小学毕业,老大还没毕业,因为他留了两级了。老二也没毕业,同样也留了级。
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有时候,我会想起他们来,想起在他们脏兮兮的手上翻来翻去的滚烫的烤红薯,还有他们家里永远不散的柴烟味。
不晓得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些院子里的生活,有一种大家庭的温馨。家与家,人与人,虽然时常不免有些龃龉,有些摩擦,但总的来说还是其乐融融的,尤其是小孩子,伢崽们都像兄弟,妹子们都像姊妹。岁月让他们成长,然后分离,当初相濡以沫,过后相忘江湖。童年的记忆不会轻易提起,却是永不忘记。
我后来工作的单位,也曾在几个院子里。最初是在宝南街的泥木工人俱乐部大院子里。一个大坪,四围全是平房。有一些单位驻在里头。我们单位是东头一线四间大房。采光不好,有些阴暗,春天里也很潮湿。但是宽敞,并不压抑。我们单位杂志社的编辑坐在桌子旁看稿子,点着台灯,抽烟,或喝酽茶,轻轻咳嗽。灯光把脸照得很亮,安静的房间里收发员走进来,同样安静地把稿件分发到每张桌子上,堆起半尺高。
我们在大坪里拍过许多集体照,留下了一排排岁月中不凋谢的笑容。
我们还搬到过望麓园六号,又搬到青少年宫后院,曾经还搬到惜字公庄。惜字公庄这名字很好听,与我们单位的工作性质近。也是长沙民国年间的大院,前后三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两个有花台的土坪。有几家单位在大院里办公。大门有传达室,门外有炸葱油粑粑的,有卖米粉的,有小饭铺同麻将室。有挑担子磨刀的汉子一边吆喝“锵刀磨剪啦——”一边抬脚朝大院里迈,守传达戴老花镜的赵老倌就会走出传达室朝汉子喊:“莫进来!莫进来!这是机关!”汉子望一望里头,转身走去,巷子深处飘起他的“锵刀磨剪”的叫声,如烟。
这大院虽大,却也安静。倒是周围有些市声杂遢,反衬得更静。院子里的几棵梧桐上,有麻雀的啾唱。我们单位在最里头一栋的楼上办公。太阳天气,我们上完厕所就站在一个好大的阳台上晒几分钟太阳,抽颗烟,然后再回到办公室做事情。站在阳台上可以望到院子外头小巷里的黑瓦屋顶。这是长沙的老街巷。有旧日子古铜色的毫光。
但我们在这里办公不到三年,展览馆路要从东往西拉通,惜字公庄的那些黑瓦屋连同我们这个大院都在红线里头,于是不久就拆迁了。
又不久,惜字公庄原址前头建起了如今的喜来登大酒店,酒店里的运达美美百货橱窗里,看得见LV和Louis Vuitton。我每回开车经过这里,都想起从前的惜字公庄,想起摊到办公室上的一方安静的阳光,想起那些黑瓦屋顶,想起守传达的赵老倌同梧桐上的麻雀啾唱。
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带有玻璃幕墙的大楼,在太阳下闪动着现代文明的耀眼光芒。
但我明白,住在这样的高楼广厦里,同住在我上面描述的旧式的大院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生活。然而你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过旧式大院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与人是熟稔的、亲近的、相生相融的。在这样的人际空间里,生命个体不容易孤独。这空间是完整的一个世界,我们彼此近在咫尺地生活。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或者长日安稳,或者鸡飞狗跳,但是那样的时光,就叫做亲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