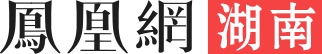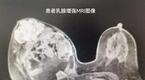孟泽:杨毓麟——一个长沙人的血性与温情


独家抢先看
作者:孟泽,知名学者,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有我无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洋务先知——郭嵩焘》《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广陵散——中国狂士传》《天人共生与道文兼济》《君自故乡来》等,曾主讲《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南方周末》“华人精英论坛”、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
杨毓麟(1872-1911),长沙高桥(今长沙县高桥镇)人,字笃生,号叔壬,又号守仁,曾先后担任《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的总主笔或撰稿人,笔名有:湖南之湖南人,三户遗民,寒灰,卖痴生,耐可,蹈海生等。
杨毓麟最为人所称说的事情有二,第一是在1902年出版了《新湖南》,辨析“湖南人之奴性”与“独立之根性”,不仅提供了“新湖南”这个意味深长的重要概念,对湖南人的性情、气质、种族、文化背景,可能的与应该的作为,作了崭新的揭示和总结,而且为启蒙革命过程之中的个人独立、地方自治、国家解放提供了理论张本,其中言及“民族建国主义”“个人权利主义”“三权分立”等,更是空谷足音。第二是1911年在英国利物浦的蹈海自杀。必须承认,“新湖南”作为对于中国社会及其前途的分析、检讨与策划,对湖湘文化的阐述,因为其理论色彩与思辨性质,加上是用文言写作,远不如新化人陈天华用白话所作《警世钟》《猛回头》那样具有感染力、感召力,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相对有限。但是,今天考量,则其内涵似乎更深沉,也更可能及于久远。其次,同样作为蹈海者,杨毓麟之死在当时所形成的波澜,不如此前蹈海的陈天华壮阔。或许,这与武昌首义、民国很快告成、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有一定关系。
2008年,岳麓书社出版饶怀民先生整理和撰著(与李日合著)的《杨毓麟集》《蹈海志士杨毓麟传》,印数不多,发行有限,杨毓麟的事迹,传播依然不广。这对于普及长沙的历史人文,了解湖湘精神的底蕴来说,自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从杨毓麟的生平事迹,从他存世的文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不寻常的热血气质——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前僵后仆,无所于悔,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种难得的理性和温情——澡雪国魂,昭苏群治,缱绻悲悯,伦理情深。如杨毓麟这样,自居“死士”,不惜牺牲,谓“男儿戮死自有方,欧刀料理翻寻常”,他们在激进与保守、自我毁灭与自我保存之间的彷徨与抉择,即使今天,也很难不让人凄然以伤、惨然以痛、肃然以敬。他们的所思所言所作为,构成了长沙历史人文最深刻、最动人的底色。而杨毓麟的《新湖南》,他的殉国,是尤其值得阐释、值得打量的经典与个案。
杨毓麟少而颖悟,据说“七岁能文,惊名宿”,13岁已遍读十三经、史记、文选,15岁中秀才,曾就读于岳麓、城南、校经三书院,“泛览国朝人经说,本国文学,历史,尤留心经世文学”。与杨姓同宗杨昌济同龄且友善,杨昌济辈分高,是“叔祖”,他自称“再侄”。两人性情不同而欢爱不衰,杨毓麟“性情激烈,个性强劲”,杨昌济厚道、温和。杨毓麟的敏感、勇力与傲岸,言论之犀利、飞扬,似乎更能让杨昌济倾慕,杨昌济在自己的《达化斋日记》记录了他们的交往。
1894年甲午,杨毓麟读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作《江防海防策》。1897年,杨毓麟25岁,中式为举人,入选二等优贡,以知县分发广西。适逢陈宝箴巡抚湖南,开时务学堂于长沙(1897年10月),杨毓麟具才名,又趋新,被聘为教习,从此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一起倡言变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时务学堂解散,“毓麟几及于难,避乡数月乃免”。1899年,入江苏学政同乡瞿鸿机幕,不久辞去。此后埋首湘绅龙湛霖教馆,午夜青灯读禁书,“以求世界之知识”。与龙氏“极相得”,劝龙氏捐资办学,“长沙胡子靖创办明德、经正两校,龙氏尝竭资以助,笃生实有力焉”。
1901年年末,杨毓麟离开长沙前往上海。第二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法政,主编《游学译编》,“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作《满洲问题》,“声政府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
1903年,沙俄拒绝从满洲撤军,留日学生五百余人集会东京,开拒俄大会,成立“拒俄义勇军”,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提出鼓吹、起义、暗杀三种革命途径,练习射击,学做炸药,派遣“运动员”,组织暗杀,声称:"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杨毓麟自认“运动员”,愿意负责江南一带策动武装起义,与黄兴等组织暗杀团,“研究爆发物十余种”,因制药失慎,一眼被炸伤,“党人能自造炸弹,自守仁始”。
就在这一年,杨毓麟曾与同志者携炸药回国赴北京,于草头胡同租屋一间,计划在故宫内廷或颐和园内一举炸毙西太后及朝廷命官。居京数月,往返京津之间,终因戒备森严,无从下手,失意南返,旅居上海。
1903年12月,应邀回长沙,筹备华兴会。1904年2月15日,参加华兴会成立大会,派往上海,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会长。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定:“计以十月十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炸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爱国协会拟在上海响应。但起义因有人告密而流产,黄兴等逃往上海。
1904年11月7日,黄兴、刘揆一、杨毓麟、章士钊等四十余人在上海英租界新闸新马路余庆里开会,决定“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不久,余庆里机关遭破坏,清兵在余庆里机关搜出手枪、炸药、名册、会章等物品,按册捕去黄兴等13人,发现杨毓麟名片多张。杨毓麟改名杨守仁,于12月上旬与宋教仁等一道逃亡日本。
此次失败后,杨毓麟认为在东南沿海发动起义终究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于是,“继乃变计,混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杨毓麟再次回国入京,受庇于管学大臣张百熙,出任译学馆教员,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策动暗杀。
1905年7月16日,清廷颁发谕旨,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分赴东西各国考察政治,稍后又加派绍英参与其事,凑成五人,俗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杨毓麟得此消息,赴保定,会晤杀手吴樾,曰“清廷伪为预备立宪,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愚吾民,恐中国永无再见天日之会也”。吴樾慨然曰“彼五大臣,可击而杀之也”。吴樾提出,与其先杀铁良,不如先杀五大臣。杨毓麟首肯,但考虑自制炸弹无电动开关,实施者终不免于难,不忍心吴樾去执行此一计划,他本人作为“北方暗杀团”团长,毅然力争担任炸手。吴樾起而制止曰“樾生平既自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察宪政之五大臣。”又曰“樾请为诸君子着先鞭,更愿死后化一我为千百我,前仆后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并建议杨毓麟设法打入载泽幕中,以便里应外合。
由于五大臣行期提前,吴樾于9月24日怀揣炸弹,乔装成皂隶,从容步入北京正阳门车站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当机车与车厢挂钩时,车身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场死难,载泽、绍英受轻伤。此时,杨毓麟已预先谋得载泽随员一职,以为内应,事件发生后,清廷并未怀疑他,杨仍以随员身份同行,12月11日出发,抵达东京。时人云“吴樾之中国炸弹第一声,即守仁之秘谋也”。
杨毓麟到达东京后,同盟会已经成立,亟待发展,杨与黄兴、宋教仁等会晤,毅然辞去随员职务,于1906年6月25日正式加入同盟会。不久,其姊寿玉病逝,他“归慰先慈,家居七日即返沪,自此不复履三湘故土”。
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杨毓麟任总主笔,于右任任经理。报纸“以沉郁委婉见长”,“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报纸创刊仅三十七天,因邻居失火而连带受灾,机器设备付之一炬,火起时,杨毓麟还在伏案疾书,烈焰封门,他沿窗外电杆逃下,免于难。报纸为此仅停刊一天,继续出版。在作为总主笔一年多里,杨一直“风风雨雨,夜以继日,四处奔波,可谓至苦”,发表大量政论和时评,内容无非痛陈民族危机,号召国人奋起,宣传革命排满,揭露政府黑暗官吏贪鄙残忍,痛斥清廷“预备立宪的虚伪和荒诞”,“以其坚确之辞义,抒其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杨毓麟乃报纸“最努力的一个人”(于右任)
1908年,杨毓麟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行赴英国。于右任送之以词《踏莎行》:“绝好河山,连宵风雨,神州霸业凭谁主。共怜憔悴尽中年,哪堪漂泊成孤旅。故国茫茫,夕阳如许,杜鹃声里人西去。残山剩水莫回头,泪痕休洒分离处。”
1909年,杨毓麟辞去秘书一职,转赴英国苏格兰爱伯汀(砈北淀)大学读书,专攻英文及生计学,借以“探社会学之奥”。1909年秋,孙中山流亡伦敦,杨毓麟与之会面,建议设立欧洲通讯社,孙中山在《致王子匡函》中说“昨日笃生兄来谈通讯社事,弟甚赞同其意”。
1910年夏天,杨毓麟利用暑假到英国农村考察,并与杨昌济一道到巴拉特度假,接触英国社会,看到底层英国人的贫困,深陷痛苦之中,既不满现实,又对未来失望,既赞美铁血,又感叹铁血革命换来的社会并不令人乐观。他曾经在诗中抒写豪情曰“山河破碎夕阳红,只手擎天歌大风。莽莽中原谁管领,龙蛇草泽尽英雄。”而此时,则心境暗淡,曰“去国意未忍,回辕当此时,津梁疲末路,醒醉动繁思。世事真难说,余心不可移。平生凄恻惯,宁与白鸥期”。
1911年,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遇难,损失惨重,悲愤交加,“精神痛苦,如火中烧”,以致旧病复发,头痛浮肿,不能成眠,痛苦难以自解,加上原本身体虚弱,“年长失学,好作繁思,感触时事,脑病时发,贪食磷硫补品,日来毒发,脑炎狂炽,遍体沸热不可耐”(他曾在1909年给妻子俪鸿的信中谈到,“请二哥买脑丸”),“惯不乐生,恨而之死,决投海中自毙”。留书托石瑛、吴稚晖将留学英国数年所积攒的一百三十英镑中的一百英镑转寄黄兴,作为革命经费,其余三十转寄其老母,以报养育之恩。之后,1911年8月5日,赴利物浦,又给杨昌济留信曰:“怀中叔祖大人:作此函与长者永诀也。守仁脑炎大发,因前患脑弱,贪服磷硫药液太多,此时狂乱炽勃,不可自耐。欲趁便船归国,昨晚离厄北淀来利物浦,今晨到车站,然脑迸乱不可制,愤而求死,将以海波为葬地。今日命尽矣,形神解脱,恩怨销亡,万事俱空,一缘顿尽,骂我由公等,不暇惜矣。旅费余三十磅,寄归与慈母,为最后之反哺,不敢提及自戕一字,恐伤母心,亦不忍作一禀。”留下此信后,杨毓麟蹈海自尽,终年40岁。遗体在8月7日为一渔父觅得,葬利物浦公墓。
杨毓麟之死,同志于革命者,顺理成章地释之为“殉国”,拟之为屈灵均。于右任回忆,人们曾经以“湘中二杨目之”,杨毓麟自别于杨度,说“彼(杨度)时髦也,我何敢望”。南社诗人高旭作《浪淘沙》以吊:“天末又西风,彻耳惊鸿。男儿羞作可怜虫。宁与金瓯同碎却,遗恨无穷。奇气化长虹,往事都空。鲁戈难返日当中。一任狂涛号日夜,淘尽英雄。”
杨毓麟作为近代中国的启蒙革命者,其所具有的不惜牺牲的烈士情怀和血性,显然有作为湖湘子弟的特殊禀赋,同时也是那个沧海横流的时代召唤的结果。
而最让人觉得不同寻常的,是他作为革命者的勇敢、决绝和不顾一切,与作为知识者对中西文明与文化清醒澄明的理性洞察,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以及作为家庭中人,作为儿子、父亲、丈夫的柔软、深情和明哲,形成鲜明的反差。两相对照,真是不可思议,是分裂的,也是充满张力的,是豪迈悲壮的,又是令人心碎的。
旅居英国时,在给儿子克念信中,杨毓麟谈到读经,谈到学好中国的传统典籍,他说“近日无知少年醉心西化,一言及四书五经,便有吐弃不屑称道之意,殊为大谬。此辈只知有欧洲,却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欧洲各国,现在中小学校,每礼拜必须有数点钟讲解耶稣教《圣经》。此《圣经》,既系宗教哲理糅合杂凑之书,又系二千余年以前陈腐学说,若以欧化少年眼光论之,宜其吐弃不屑矣。然彼中方且崇拜之,诵读之。何况四书五经为周秦以前政治、文化、历史、道德、伦理之所荟萃,于世界各国中流传最古之学说,实蔚然为一大宗者,而可弁髦土苴之乎?吾国文教,推崇孔子,孔子并非宗教家,其生平所注意者,全系政治、文化、道德、伦理诸问题……无一书不切于人事者。专注意生人治乱安危问题,而不肯妄谈人道以上之议论,系吾国有史以来各大学问家特别可贵之性质。”对于传统的尊重,并不妨碍杨毓麟对于现实,对于新世界的关切,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人事必以现在者为主,故宜详于今日世界事情,而古代无妨稍之从略。”这样的说法,类似于我们今天说少醉心中国历史,多关注世界文明。与此一致,杨毓麟在《论道德》中对于传统的纲常名教,作出了明确的批判,“有天然之道德,有人为之道德。天然之道德,根于心理,自由平等博爱是也,人为之道德,原于习惯,纲常名教是也。天然之道德,真道德也,人为之道德,伪道德也。”而伪道德,“其惑世诬民,则直甚于洪水猛兽。”
在他留下的不多书信中,难得地呈现了与其整个激烈的革命生涯不同的极其温情的另一面:和母亲说伦敦空气不良,所以每天到公园散步一点钟,始觉佳适;和妻子孩子谈家常,对于孩子的教诲、规范和希望,尤其恳切动人:
让孩子不要依赖外家,最好送入新式学堂,“凡人贵自立,不宜使倚傍他人作生活。英国人教养小儿女,一切必令小儿女自己支持自己,自小习惯,自然养成独立自治性质。”
要求孩子在新式学堂里学习好算学、英文、体操、格物,反复强调体操的重要。同时叮嘱孩子,要学会做人:“不可在学堂内与同学诸人终日闲谈乱讲,不可与同学诸人闹意见,待同学诸姊妹宜格外客气,彼此以求学用功相勉励,见学堂监督教习,尤宜恭而有礼,恪守校训,不可违抗……一切日用饮食起居,须有一定规则,按照一定钟点。钟点是人生在世上一件必须谨守的事,人无一定做事钟点,便是不能学好的凭据。”“晚上休息上床,不可胡思乱想,须认定一段格言,或认定一个算学题目,用心思索,自然安然入梦,神魂清爽。平日除与诸女同学往来,不准尔与男学生往来,亦不准妄向别的人家行走,违背我的规矩,便不是我的女儿。”
教导孩子怎么学写作文,“作文全在多看古文,多明事理。多看古文,乃能知文法,多明事理,乃能深切事情。”
告诉孩子当知生于忧患,“孟子有言孤臣孽子,操心危,虑患深,故达”,又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须立志学做圣贤豪杰,须自恪守钟点做起,孔子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告诉孩子不可妄言,不可自夸自诩,不能自以为是,必须“谨慎小心,说话尤宜谨慎。每说一句话,必想了又想,愈迟愈妙。因凡事必从忙里错过,凡说话亦从忙里错过。驷不及舌,悔之无及。谨言慎行,是孔子教人千稳万当法门。”“为人须要切实,须要虚心求益,不可听教习夸奖一二语,便忘却自己是一事不知之蠢物。世上道理多,事情多,无论是何等绝顶天才,不过晓得十万分之一,学得百万分之一。且即此十万分之之一,百万分之一,若非细心研究,切实履行,时时刻刻以扎硬寨打死仗方法对待之,尚且不能得手。”“一个人的知识,对于世界上真理,总不能得有千万分之一”。世上聪明人多,切实成一个有用的人却不多。
教导孩子懂得知识与德性对于人生的重要,懂得如何得到正当之知识及坚强之德性:“时局多艰,民穷财尽,能得一好学堂读书,便是人生幸福。吾儿万勿偷闲习懒,必须勇猛精进,发愤修学,为目前立身要策。凡人一生持身处事,皆须有正确之知识,及坚强之德性。知识不正确,则于判断是非,推察人情事理,必多谬误;德性不坚强,则一切知识,皆是浮光掠影,自己一毫不能受用,一旦遇国家有事变,全然担任不起。欲得有正确之知识及坚强之德性,皆须由学问上得来。科学中如算学、几何、物理、化学等等,皆所以启发人生正当之知识。如古代名人传记及宗教家哲学家之遗训(如《四书》即是),皆所以扶植人生坚强之德性。平日读书修学,切实有恒,一刻不间断,一点不草率,即是养成坚强德性之一项方法,如修学不能有恒,用功不能切实,则其人必非佳士,因其德性之不坚定,只此一端,已可概见。”
他还叮嘱孩子,不可贪看无聊小说。
此种私人范围内的忠告和诉求,彰显了杨毓麟并不异于常人的理性与深情。也许,所谓特立独行,所谓传奇身世,其实都是成长在常识常情的范围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