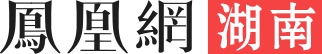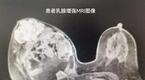王鲁湘:风雨赋长沙


独家抢先看
作者:王鲁湘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凤凰岭书院院长。
一
“远山崷崒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掛海棠前。”这是唐代名臣、大书法家褚遂良的《潭州偶题》。长沙在唐代称潭州。“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唐代诗人杜牧这首《山行》远比禇遂良的《潭州偶题》著名,在中国几乎妇孺皆能背诵。是不是写的岳麓山景,不好说,不过,清代大才子袁枚劝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将当时的红叶亭改为爱晚亭,却是缘于此诗。如果有好事者要评选中国十大名亭,我想爱晚亭是笃定入选的。过去在湖南生活,感觉四季之中,长夏和冬天色彩单调些。长夏一片墨绿,而冬季稍现青苍,但还是绿的基调。春天和秋天都不长,山里的野桃花刚一绽放,桃花雨就下来,炎夏接踵而至。春天印象最深的是二月里的桐花。由于桐油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商品,所以自古桐树就是湖南最重要的经济林木,山前屋后,都能看到桐树娟修的身影。桐花二月里开,花大,色白,白得有些凄惨,而且招雨。印象中桐花白色的面庞总是在风雨中恍惚。早春二月的细雨,很冷很冷,是那种一点一点浸到骨髓的冷。桐花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日子绽放,倒真有点“敢为人先”的烂漫。故尔章士钊在《题湖南六家词》里会吟出“桐花湘雨情何限”的句子。这大概就是湖南的春天给人的印象。湖南的秋天除去“二十四个秋老虎”,真正秋高气爽的日子不多。好在有满山的秋枫红叶。枫树是真正的栋梁之材,高大挺拔。叶子春天嫩绿,夏天墨绿,秋天丹红,冬天落尽。秋枫之红,有一种烈酒的性格,不是那种很纯正的红。如果说纯正的红是100度,那么秋枫的红就是120度、150度。我小时候曾用菜刀割过百年老枫树的皮,淌下的树汁竟是牛血一般的颜色!几场阴冷的秋雨和薄霜过后,枫叶的红色会变黯,会从透明的秋空中飘落,旋着三叉戟形状的身体坠下,坠下,在空中不断翻腾出俊俏的身段,然后平平地躺下,一层,两层,直至厚厚的铺满大地,把烂漫在半空中的激情,降解为更为深沉的泥土。生活在湖南时,我从未想过二月天的桐花和霜天的枫叶同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性情有什么联系。当我读了刘汉辉编的《长沙百咏》诗集之后,开始回味这种感觉。唉,好一个“烂漫桐花二月天”,又好一个“霜叶红于二月花”!
二
“风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华供转徙,眼界得清新。试问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这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一首《怀岳麓》,大概是朱子离开湖南后,为怀念在岳麓书院讲课的日子而作。那种自在江湖、悠然长啸的潇洒自由的学术生涯,总是让他心驰神往。一个理学家,在诗中又是风月,又是江湖,又是春水,又是长啸,好像有点不搭调。其实,这正是中国士大夫一种哲学本体论的生命情调。朱熹在岳麓书院时,曾同书院山长张栻一起登上岳麓山的赫曦台,并同张栻联句唱和:“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眇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显然,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怀古忧时之情,更像一个儒家士大夫。从朱熹的两首诗中,我看出了湖南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心目中的双重意象。当他身在湖南山水之中,他会触景生情,时时会从心底泛起怀古忧时的家国之思。而当他同湖南山水保持一定的距离做一种遥遥眺望时,他又会认为那是一片远离中心的江湖。
说起江湖,中国大地上大部分的地区或有江而无湖,或有湖而无江,湖南要算是一处有江有湖,江湖连属,出江入湖,出湖入江,江湖一片水云乡的好地方。湖南处江湖之远,古代人们无论是出是入,无不舟行。从长江入洞庭,再沿湘、资、沅、澧、汩罗诸水,可以一棹而抵湘中、湘南、湘东、湘西。古人在湘流徙宦游的踪迹,基本上也是沿水而行。故《长沙百咏》所选诸作,竟有相当篇什与江湖和舟船有关。我想,这样的地理环境,一定给流寓湖湘的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文化心理上,中原人士的南极是潇湘、衡岳,所谓“雁知春近别衡阳”。春天要来了,连鸿雁都知道要告别衡阳北飞了。在唐人看来,潇湘仍然是遥远的地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唱道:“斜月沈沈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渤海边的碣石山是文化心理上的北极,潇湘是南极。说潇湘是南极,意思是它仍然属于中原文化区,只不过是中原文化区的最南缘罢了。过了潇湘,如岭南,如黔贵,那就是荒服檄外之地,另一个文化区了。于是,湖湘景物,在古代文人心目中,便是中原文化意象中最野逸、最自在的了。如米芾所题《潇湘八景》。但是,即便在米芾描画的“际以天宇之虚碧,杂以烟霞之吞吐,风帆沙鸟,出没往来,水竹云林,映带左右”的潇湘景象里,也仍然沈潜着自远古舜帝至唐代诗人李白的中原文化记忆。所以“江湖”是一个不同于“蛮荒”的文化意象,它不是中心,但也不在圈外,这是理解湖南地缘文化特性的关键。对于圈外地区来说,湖南人,尤其是湖南士子,可能是中原文化最悍勇的卫道者;而对于圈内来说,湖南人,哪怕是学富五车的湖南才子,也会被看作“南蛮子”。
在中国文人心目中,一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家国的,从家庭伦理到社稷礼法,个人有承担的责任。诗文中出现的“高堂”、“庙堂”、“魏阙”、“关塞”、“城郭”大概都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且命之为“家国世界”;另一个世界是属于江湖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家庭伦理与社稷礼法需要文人个人去承担,身是漂流的,心是放逸的,文化意象常见的有“江湖”、“扁舟”、“芦荻”、“平沙”、“湖浦”、“钓翁”。在古人眼中,湖南风物与此“江湖世界”最相吻合。所以,湖南全境,而非其某山某水,便成为古代文人心目中与“家国世界”不同的“江湖世界”。只要有人迁谪湖南,或途经湖南,只要有人给在湖南流寓的人写信寄诗,或只要有人因为某个原因想起了湖南,也不管他是否到过湖南,他们都会把这一个“江湖世界”的文化意象加到湖南身上。问题是湖湘这个“江湖世界”不同于吴越那个“江湖世界”。吴越江湖是温柔缱绻的,有红袖夜添香与酥手摘莲蓬,是可以归隐与终老的。湖湘不是。这个“山川佳绝地”对文人来说还是野了点。这里的山水不像吴越山水那样可以亵玩于文人掌袖之中。更要命的是,湖湘是屈贾伤心地!如果换个别的什么人伤心也行,偏偏是中国文人心中品行、才气超轶绝伦的两大文豪,这伤的可就是全体文人的心了!伤什么心?伤的就是身处“江湖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家国世界”的心。“万古惟留楚客悲。”唐代诗人刘长卿一首《长沙过贾谊宅》写出了历代文人在湘的共同心境,那就是刻骨铭心的孤独:“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屈原贾谊的悲剧命运与湖湘山水遭遇相逢,湖湘这个“江湖世界”也就命定地染上了千古难磨的人文悲情。文人只要掉进这个江湖世界,就会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描述的那样,是进亦忧,退亦忧,他在湖湘这个“江湖世界”绝对放不下对“家国世界”的怀念。他总是在两个世界中徘徊,时而忧愁时而放达的心态反复撕裂,这在贾谊的《鵩鸟赋》中表达的最为淋漓尽致。我想,在这样两个世界里低昂容与,兴尽悲来,是否造就了湖湘文化的张力,而成就了湖湘人士独有的性灵?
三
笑傲江湖,潇洒倜傥中已自有一层孤独;在江湖世界苍茫独立,又满脑门子的家国天下,孤独中更平添一层惆怅。“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唐·钱起《归雁》)古今士子好像只要一站在湖湘的土地上,就莫名地涌出一种苍茫独立的感觉,这感觉,是很有一些道德上的清高感和责任上的使命感的。屈原放逐沅湘之间,苍茫独立,“怀质抱情,独无匹兮”,“定心广志,余何惧兮”(《怀沙》)。贾谊竢罪长沙,苍茫独立,“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吊屈原赋》)。张孝祥泛舟湘江,苍茫独立,“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水调歌头·泛湘江》)。辛弃疾守长沙,苍茫独立,“风流已自非畴昔,凭画栏,一线数飞鸿,沈空碧”(《满江红·暮春》)。谭嗣同游湘江,苍茫独立,“天地莽空阔,飘然此一舟”(《湘水》)。黄兴做出惊人事业后回到湖南,唱罢《大风歌》,又赋《归去来》,在鱼龙寂寂、猿鹤依依的夜晚,“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回湘感怀》)。蔡锷二十三岁,练兵长沙,戎装驱马岳麓山巅,苍茫独立,慷慨而歌:“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蔡和森为求救国之真理,从师于万里之外的法兰西,在海轮上回望神州,苍茫独立,“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少年行》)。毛泽东少年风华,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霜天寒秋,苍茫独立于橘子洲头,“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多年来,我一直想不明白,何以湖南士人拥有这样一种群体的性格?他们总爱把自己预置于宏大的宇宙情境之中,渺小的个人空无依傍,遂生出巨大的孤独感,然后浩然正气沛然而出,充塞天地之间,舍我其谁的豪情顿时化作担当牺牲的勇气。现在我想我可能明白了一点点,那就是自屈原贾谊以来,湖南士人只能在苍茫的江湖世界的宇宙情境中去遥想远在中原的家国世界的命运。他们的思想必定从天地寥廓的渺远之道入手,把入世义务和个人责任的终极根据同此苍茫宇宙之大道联系起来,赋予一个永恒的意义。也就是说,士人在家国世界安邦济世的行为,一定要有一个在江湖世界道通天地的哲学依据。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没有正气,没有正气便行不刚烈,行不刚烈则不能成大事。所以湖南士人无论是立志、励志还是酬志,都会习惯性地先把自己放在同家国世界的中心有一定距离的江湖世界里,苍茫独立,寻找终极意义,在巨大的孤独感中养吾浩然之气,然后以比任何人都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走向他与家国世界的斗争。他甚至于连这斗争的胜负都不在乎,尤其是结局的功利目的,那更不在话下。屈原斗争的结局是怀沙自沉,牺牲生命而完成其道德人格;王夫之武力抗清失败,退而著书,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对中国文化进行沉痛反思,完成四百多卷著述,殁后遗书散佚,二百年无人知其名姓,却有一股天地正气长存人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殊死作战,屡败屡战,对战争之结局并无胜算,但“奋起以卫吾道”而已!谭嗣同变法失败,自请流血以昌国,甘当死者以酬君。黄兴于缔造民国有首功,每役必身先士卒,最后鞠躬尽瘁,作为民国的道德完人而名垂青史。蔡锷拔剑南天,反袁护国,以一隅而抗全国,“明知无望,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至于后来共产党人夏明瀚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瀚,还有后来人。”则更是这种殉道精神的体现。湖南士人求道、践道、卫道、殉道的精神之勇毅刚烈,是大大强于中国其他地域士人群体的。这可能同湖湘地区这一江湖世界同中原的家国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有关。距离太近则易俗,未免功利主义掩过超越的宇宙意识;距离太远则易飘,高蹈远引而失去对家国世界的责任感。湖南的距离正好,中心对它有足够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湖南士人无不以北渡洞庭长江为实现个人抱负的人生动力;但它又确实是边缘,三面环山,一面阻水及与苗、瑶、土家、侗族杂处并混血的地缘文化环境,相对封闭,自成世界,容易养成特立独行的人格。加之自屈贾以迄岳麓书院,湖湘文化中特别重视道德人格的建树,并把这一道德人格同宇宙中生生不息的气与常存不灭的理联系在一起,使湖南士人在求道、践道、卫道、殉道时,常常视死如归,甚至于到了以流血牺牲杀身成仁为至高无上的美学境界的痴迷程度。湖南士人不仅蹈厉敢死,而且死得英勇壮烈。谭嗣同“流血请自嗣同始”,唐才常笑而受缚,大呼“天不成吾事”而就义。此二人都是可以逃脱却选择死亡的维新烈士。辛亥革命党人禹之谟受绞刑时质问刽子手:“我要流血,为何绞之?吾热血不流,辜负我满腔心事!”辛亥革命时期为警醒同胞而采取自戕行为的著名蹈海三烈士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都是湖南人。“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就是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南才子杨度写的《湖南少年歌》。湖南士人生命情调中有一种铁血精神,有一种军国意志,有一种强悍的性格,湖南人自谓为“霸蛮”。这种生命情调,使湖南人自19世纪下半叶起,成为国家栋梁和长城。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湖南人的身影。《湘军志》云:“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
湖南士人生命情调中的铁血精神,有一种大悲怆与大沉痛。我不能确切地说清楚这种大悲怆与大沉痛是否同湖湘学派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湖南士人自小受到的教育都暗含着这样的激励:你虽身处江湖,但一定要心怀魏阙;你不会是最初被委以重任的人,但你一定会在不堪收拾的时候自己站出来,去完成那些只有湖南人才敢去做的事!以我在湖南生活的经历,我深知那样的山水,那样的江湖,那样的气候,那样的传说,那样的民风,是必然要激荡出那样的清怨之气、孤愤之气、风骚之气、南楚霸气和天地正气的。湖南士人活的就是这口气。
行文至此,忽地又想起“烂漫桐花二月天”和“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那惨白的桐花和血红的枫叶,总使我想起湖南士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