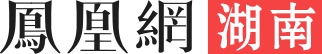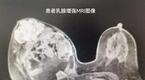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岩中花树》:桃花落下 树木汗毛一样竖起
原标题:《岩中花树》:桃花落下,树木汗毛一样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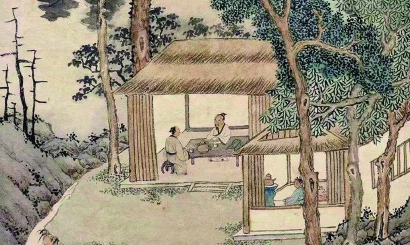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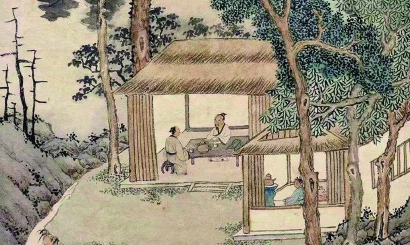
◆文征明 品茶图
文丨毛文琦
赵柏田的笔下的“岩中花树”,是16至18世纪江南文人开出的“一树树好花”。他的写作,相当贴合钱锺书所说的“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冬日午后读赵柏田的《岩中花树》,仿佛钢琴键有力落下复又弹起,凝练绵密的文字编织出一张16至18世纪的网。明中叶到清康乾时期300余年的历史中,作者在山阴道上撷取江南群英,从王阳明到张潮,选取几个支点,悬起了这张意义之网。近十几年来,赵柏田的写作链条一一延展,从更早之前的《历史碎影:日常视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到后来的《大明王朝之春夏秋冬》《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中国往事三部曲》,他的非虚构写作中满蕴史识与诗意,在历史空白处追寻幽微复杂的人性与情感,丰富了当代文学,成为一个极好的剖示范例。
恰好在文中的附录里,读到作者的一首诗《芳香的年代》。细细品来,开头与结尾的两句,“把铜镜擦亮,掸去花瓣上的尘土,往浴缸里撒上沉香屑”与“桃花大雨一样落下,树木汗毛一样竖起”,庶可与这本书带来的阅读体验相联系。
“把铜镜擦亮,掸去花瓣上的尘土”
这首诗出现在王阳明篇后,作者原是用来想象明朝“浸染着精致的文人趣味的市井生活”的。但当看到“镜”这一意象时,不由想到作者多次申述的“纪实与虚构”。赵柏田自己也多处提及“镜”,尤其他另有两集,分别名为《万镜楼:历史的纪实及其虚构》和《纸镜子:七个故事》。
当历史的铜镜被擦亮,作者用自己的心镜去观照历史中的风流云散,去打捞历史长河中的歌哭笑谈,去体味雨打风摧花瓣委地时一脉芳香不散,谁能说历史之镜依旧在沉默?它封闭而又敞开着,作者带领我们穿越这面镜子,触摸那古老日常的生活,体会博尔赫斯说的“普通的陈旧的日常生活节目,会包含着反影所精心制造的一个虚幻而深刻的世界”。博尔赫斯,正是作者奉为写作导师的南美作家。
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实,赵柏田在《岩中花树》的自序中提到:“如果说传统是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是移动的,不管我们行进了多远,总可以在里面照见我们‘曾经是’的模样。从这一初始的映像,还可以看见我们‘现在是’或‘将来是’的模样。”
作者正是怀抱这样的史识,在叙述中重返历史现场,并且因为文字的老道与叙事的成熟,使得我们在阅读时拥有了一种摇曳生姿的体验。赵柏田说,纪实与虚构,是他努力打通的“任督二脉”。毕竟,从太史公起,到林语堂、史景迁、盖伊·特立斯,史传文学本来就是非虚构写作的渊薮,而“新新闻主义”则提供了新的养料。“虚构就是再现往事,它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所谓羚羊挂角,相由心生,他们不过是心灵世界的一个镜像。”赵柏田的文字呈现了史笔与诗心的交织,虚构之处给人真实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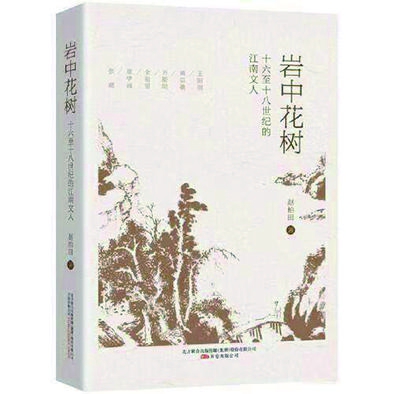
文字会呈现自己的力量。比如王阳明篇中“黄昏不是从天上盖下来的,它就像一棵树,从河面向上生长,顷刻间就笼盖了四野”;再如张岱篇中“一路但见林间漏下的月光落在地上,疏疏如残雪一般”;再如黄宗羲篇中“八月的大海如同一面潮湿的镜子,坐在船上的两个人都从对方的眼睛里映照出了自己的落魄”。这些句子营造了当时的环境,让人想到前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中沙梅拾取金粉,打造金蔷薇这个聚金成花的故事,“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
诺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历克谢耶维奇曾说:“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历史学家保罗利科也认为,历史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在作者笔下,章学诚谈论那副为蔡知州所作的画时说,画就像梦和镜子,都属于“幻”,都是既像真实又不是真实的东西。他认为一幅画的好,就在于变动中抓住了一个人的内在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柏田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在叙事中涌现出来的历史,在电光火石间抓住了永恒。
“往浴缸里撒上沉香屑”
往浴缸里撒上沉香屑,取的不过是氤氲的香气。
在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中,开篇的王阳明与末篇的张潮,正好前后呼应,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而对于王阳明的写作,作者曾说自己开展了一次冒险,当然这种冒险是值得的,正如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诺奖受奖演讲中说的那样:“我们把这种个人化的视角、这个我当作是最自然、最人性化、最真实的表达,哪怕这种表达放弃了更为宽广的视域。以这样的第一人称来讲故事,就好像在编织一种与众不同的花纹,独具一格。”
作家叙事的冒险,不免还带着莽荒时期的粗粝。比如行文中偶见引用西典,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乱感。如王阳明少年期间的自述,“我就像把风车当作魔鬼的唐吉诃德一样打马向他们冲去”,龙场悟道前的牢狱之灾阅读《周易》提及“要像纳博科夫说的那样用脊柱骨去读它”,再如不说成功学而说“卡耐基式的指南”,诸如此类的“沉香屑”式话语在流畅的阅读中跳将出来。
好在此书后面都是第三人称叙述,而到了写作张潮篇时,一方面随着作者的文笔更为成熟,驾驭语言更为轻松自如,另一方面读者对王阳明与张潮的阅读期待自然不同,正因此,张潮篇读来圆融清劲,沉香香味萦绕,而张潮汲汲于自己立身出处的心路历程,竟让人生出异代同悲之感。最终张潮借《幽梦影》名传于世,尤其在微博微信时代,人们蓦然发现这个奇特的文本范式仿佛是早生了300年的朋友圈,他借张潮之口说:“书中最初的评语和新近补入的一批评语已经时隔十年,在这十年中,有些朋友已经去世了,但在这本书里,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他们虽死犹生,继续与年轻的一代进行着热烈的对话和辩论,他们的智慧不时在书页中闪烁。我想,这是《幽梦影》的最大魅力之所在,不是我张潮一个人写下了它,而是一个时代的文人们共同写下了这本书。”张潮的盐商身份与前面全祖望篇作为不可忽略的背景的扬州大盐商们正好前后呼应,共谱了16至18世纪江南一代富商对文化的扶持与推介之曲。
将潜藏的思想史传承相勾连
歌尽桃花扇底风,中国的土地上永远有一树桃花灼灼其华。而“桃花大雨一样落下,树木汗毛一样竖起”竟暗合了赵柏田笔下的晚明生活史与思想史。他说他愿意用“风华而奢靡”来形容晚明南方的士人生活,这一部分内容集中呈现于《感官世界:晚明士人的物质生活》这一章中,所占不过全书八分之一,内中篇幅相对短小,但无论是冒襄与董小宛“品香”,张岱饮茶及“金山夜戏”,文震亨的《长物志》,还是戴名世的纸上园林,性灵派袁氏兄弟的感官世界,享乐主义李渔的“列仙之福”等等,都给书中世界镀上了一层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底色。这部分内容恰与作者后来的《南华录》遥相呼应。如果说那一树桃花背后是一代江南文人生活史,作者目光如炬地在袁小修一节中描画了他们更为完整的内心图景,即“一边在世俗生活的经营中耽于世俗的享乐,一边又时刻等待着来自权力中心的召唤”。而王阳明篇中“精神是光,世俗是黑暗,光可以利剑一般劈开黑暗,但没有黑暗也就没有光,如同没有黑夜也就没有了白昼。又比如,荷叶承载着一滴水珠,世俗生活也是这般承载着我们的思想,如果没有了肥大的荷叶在底下托着,那还有什么水珠呢?”这样的语句,让人体会到作者笔下文章的心意。
当然,《岩中花树》的其他篇更多的是让人体会到像汗毛竖起一般的冷冽,正如作者说的他想呈现的是“清峻的、坚硬的”江南,因此无论是心学大师王阳明,还是死亡道德剧中的张苍水,抑或是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汪辉祖、张潮,作者都写出他们了曾有的入世抱负,命运的蹭蹬并最终因为著录在思想文化史上获得了永生。在这本书的阅读中,可以看到作者有意识地将潜藏的思想史传承相勾连。比如写道黄宗羲把张苍水这19年来的“三度闽关,四人长江,两遭覆灭”的经历形容为“吹冷焰于灰烬之中”。而张苍水的女儿是全祖望的族母,自全祖望16岁那年坐听族母谈忠烈遗事,他持续一生的搜求乡邦文献和有关“故国遗事”的著述工作,当是“从这个时候埋下了最初的种子”,并写出了完整的张苍水传记。
这股冷冽的气息贯穿全书,并因为作者有意无意地选取“死亡”这一主题,因此全书读后心境更如月华照水般清冷。无论是王阳明还是黄宗羲,都有对死亡的思考。而张苍水篇的浓墨重彩更让人直面晚明“暴力的血腥、道德的血腥”,在赵柏田的思考中,“文人既是承受者更是制造者……因为这死里彰显的节义和道德,已经覆亡的前朝需要它,以教化治天下的新朝同样需要它,它是超越朝代的。因此这死是隆重的,也是充分尊重赴死者的意愿的,在故事落幕时他将得遂平生最大的心愿”。也许对博尔赫斯的学习事实上浸入了作者的思考,因为“死亡”也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情节。
说到“花树”,自然会想到王阳明那段著名的故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赵柏田的笔下的“岩中花树”,是16至18世纪江南文人开出的“一树树好花”。他的写作,相当贴合钱锺书所说的“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明末清初,晚清民国,事实上还有“沉默的大多数”仍在黑暗中等待打捞,在晦暗中等待擦亮,等待走向合适的叙事者,重新获得绽放的生命。赵柏田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