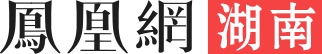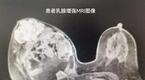郭嵩焘的出使日记《使西纪程》曾遭遇毁版
原标题:郭嵩焘的出使日记《使西纪程》曾遭遇毁版
文丨杨锡贵

对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毁板问题,学者们以往的研究,尚存在因史料不足而有叙述舛误之处和认识上有待深入的地方,本文根据所掌握的研究料特别是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在弥补以往研究缺陷的同时,力图作系统爬梳,并加以评述,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使西纪程》的编录及其主要内容
光绪元年正月十七日(1875年2月22日),在云南发生了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被杀事件。事件发生后,英国方面要求清廷 派使臣赴英国谢罪,这一差使落到了以“洋务精透”著称的郭嵩焘头上。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以望六之年、老病之身,在上海虹 口冒着风雨登上英国邮轮Travancore号,历经海上风涛的颠簸和绕行半个地球的航程,中国使团一行于十二月初八日(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 伦敦。
在朝廷决定遣使的同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奏定:“请饬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其国内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内 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一并咨送。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即办理一切,似不至漫无把握……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1]本就有记日 记习惯的郭嵩焘,自在上海虹口启程的那天开始,每天坚持写日记。一路上的见闻、观感及与随员的谈话议论,他都在日记中加以详细记录。到了伦敦后,他将从上 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 [2]。大概至迟在光绪三年(1877)的农历三月份,《使西纪程》一书便由同文馆刻印出版了。
在《使西纪程》一书中,郭嵩焘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深邃的目光和执着追求真知的精神,对沿途所经过亚洲五国、欧洲六国、非洲七国的自然地理、民情风俗、宗 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均作了平实客观的详尽纪述,尽可能让国人对世 界有更多的了解。
同时,郭嵩焘对这些见闻也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看到英国舰船相遇后,互相使用旗语互致问候,而有“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 [3]的感叹;在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锡兰看到过去的王宫仍在,则得出了“西洋之开辟藩部,意在坐收渔猎。一切以智力经营,囊括席卷,而不必覆人之宗而灭其 国,故无专以兵力取者,此实前古未有之局也” [4]的见解;当他目睹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秩序井然,“条理之繁密乃至于此” [5],深感管理组织之严密;刚一到达伦敦,即折服其“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阛阓之盛,宫室之美” [6]。
除此之外,郭嵩焘还大发议论,其中的两三段,“多朝廷所未闻”,亦是何金寿疏称“尤谬者”、李慈铭日记称“尤悖者”。
其一:“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而窟穴已深,逼处凭陵,智力兼胜,所以应 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者,京师已屡闻此言。 召公之诫成王曰:祈天永命。祈天者,兢兢业业,克抑贬损,以安民保国为心。诚不意宋、明诸儒议论流传,危害之烈,一至斯也。”[7]
其二:“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争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战 国殆远胜之。而俄罗斯尽北漠之地,由兴安岭出黑龙江,悉括其东北地以达松花江,与日本相接。英吉利起极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诸部,尽有南洋之利,而建蕃 部香港,设重兵驻之。比地度力,足称二霸。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蹠,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其构兵中国,犹 辗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轻重缓急,无足深论。而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 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8]
通观《使西纪程》全书,郭嵩焘提出和表达的观点主要为:西洋也有二千年文明,视外国人为夷狄是愚昧无知的“虚骄”;西洋“政教”优于中国,而其人民与国家 同其利病,故国运长久,这是其强盛之本;国家要强盛,第一要务是要对政治制度加以改革,建立起类似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将西方国家拒之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 的,因为西洋科学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必须对外开放,学习其立国之本,富强之术;对于西方的挑战,不能一味主战,应该讲究应付之方,不能将据理 力争定性为投降主义(即郭嵩焘所说的“不得以和论”)。所有这些,无不是忠肝义胆的肺腑之言,无不体现郭嵩焘浸淫于洋务几十年的远见卓识,忧深思远之怀, 力透纸背。认识容有不当之处,甚至有学者的酸腐之气,但“基本上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优于中国封建制度的客观事实。”“它象清风刮去了天朝虚饰的雍容外 表,暴露出它的腐败与黑暗,因而捅了马蜂窝。”[9]
二、在朝野攻击下毁板的经过
总署钞寄《使西纪程》后,李鸿章得以先睹为快,并大加称赞道:“总署钞寄行海日记一本,循览再四,议论事实,多未经人道及者,如置身红海、欧洲间,一拓眼 界也” [10];在1877年7月11日的信中,他更鼓励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20年来自己仍冲破重重阻 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因此更感郭的“崇论闳议,洵足启发愚蒙” [11]。但很可惜,能如李鸿章一样欣赏的人少之又少。《使西纪程》出版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谩骂之声遍及京城内外。尤其是在京师,朝野舆论哗然,义 愤填膺,甚至到了无不切齿、口诛笔伐的地步。这些反对者之中,既有郭嵩焘的朋友和同道者,更有他的政敌。
朋友和同道者,如湖南著名学者时在长沙的王闿运在四月二十八日(6月9日)读了之后认为:“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12];浙江著名学者时在京师的李慈 铭在六月十八日(7月28日)日记中更是斥其“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意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 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刻者又何心也!”[13]主张“筹洋”“变法”的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当年亦曾 认为书中所说言过其实,他在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日(1890年5月1日)的日记中追忆道:“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诋排, 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 [14]。由此可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称“今民间阅《使西纪程》,既无不以为悖” [15],所言不虚。
在朝廷内部的顽固守旧大臣中,反对最烈的当属李鸿藻为首的一干人。李鸿藻是清政府中有影响的重臣,同治皇帝病重时,曾以帝师身份代批奏章,可见慈禧对其倚 重之深。“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16]李鸿章致郭嵩焘的信中说:“执事日记一 编,初闻兰孙大为不平,逢人诋毁。何君乃逢迎李、景,发言盈庭。总署惧而毁板(版)。”[17]郭嵩焘给南洋大臣沈葆桢的书信中说:“近得何金寿参案,其 诋毁乃益加烈,朝廷一一见之施行,由李兰生从中主持之,故副使刘锡鸿近月鸮张愈甚。”[18]此处所引两信中的“执事”指郭嵩焘,“兰孙”、“兰生”均指 李鸿藻,景即景廉,时两人皆为总理衙门大臣。“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和“从中主持之”的,均是李鸿藻,由此可见其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上引信件中的“何君”即何金寿,时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官,是清流党“四谏”(其他三人为张佩纶、黄体芳、宝廷)之一,与李鸿藻的关系十分密切。何氏是如何 逢迎李、景,攻击郭嵩焘的呢?我们有幸找到了何金寿当年所上的那份奏折,时为光绪三年五月初六日(1877年6月16日)。该参折原文如下:
“奏为使臣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近见兵部侍郎郭嵩焘所撰《使西纪程》一书,侈言俄、英诸国富 强,礼义信让,文字之美;又谓该国足称二霸,高掌远蹠,鹰扬虎视,犹复持重而发,不似中国虚骄自张。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中尤谬 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情形绝异,逼处凭陵,智力兼胜,并不得以和论等语。我国与各国和议之成也,内外臣工痛念庚申之变,皆思卧 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今郭嵩焘敢于创为不得言和之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至祈天永命等 语,更属狂悖。夫所谓祈天永命者,谓当敬天修德,以图立国保民。即所谓自强之说,并非克抑贬损,委屈事敌,苟且以求旦夕之安。诛其立言之隐,我大清无此臣 子也。窃思古人使于四方,原在不辱君命。今郭嵩焘奉使之后,痛哭登舟,畏葸情状,久为敌人所笑。又自知清议难容,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以自文其短,而挟以 震骇朝廷,为将来见功地步。此等居心,已不可问。乃复著为书篇,摇惑天下人心。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臣愚以为中外情形, 人人所知,但在努力自强,无待反复多论。即确有所见,祇当密疏上陈,不应著书彰暴。况其中委屈情事,有谋国者所宜言,而断非使臣宜言者。相应请旨,立将其 《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光绪三年五月初六日。” [19]
从这份参折中,我们不难看到其用心之毒与出手之辣。他首先指责郭嵩焘在书中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 为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最为荒谬;第三,“不得言和之论”,在他看来“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 之气”;第四,“至祈天永命等语,更属狂悖”。除罗列以上罪状之外,何金寿进而指出,郭嵩焘是在故意张大恫吓之词,是为了“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 心”,灭自己的志气,长洋人的威风,实乃居心叵测。“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并义愤填膺地表示“我大清无此臣子也”。 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请求朝廷立即下令,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郭嵩焘在何金寿眼中俨然成了天地不容、万古不赦的叛徒、内奸、公 贼。
在今天看来,何金寿所认为的那些罪状,恰恰体现了郭嵩焘超前的思想认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敢言的担当勇气。在当时风气仍然闭塞、士大夫们仍然充满虚骄之气 的朝野上下,何金寿的这一参很是迎合了很不喜欢有人说西方世界好话人的胃口,并迅速流传开来。在京城,郭嵩焘被“同指目为汉奸之人” [20]。远在长沙的王闿运在光绪三年六月十二日(1877年7月22日)的日记中留下了 “樾岑来,言何金寿本名何铸,昨疏劾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 [21]的记载。
以上议论和疏参,无疑形成了不利于郭嵩焘的一边倒的舆论。那么主管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们又是什么态度呢?
在郭嵩焘出使期间,总理衙门的主要成员有奕訢、宝鋆、董恂、毛昶熙、沈桂芬、李鸿藻、景廉、王文韶、周家楣、成林、夏家镐等人。在这些人当中,王文韶在湖 南任巡抚时即曾与郭发生过矛盾,郭嵩焘出使前景廉即曾上折参劾过他,是坚决反郭的;景廉是李鸿藻的盟兄,而王文韶是沈桂芬的门生,是沈在军机处找来的帮 手,所以,原本属于南北两派政见不合的李、景、沈、王四人都不与郭为善,而毛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总理衙门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郭 势力。在这些反郭势力中,又以李鸿藻的作用最大。
在当时的总理衙门大臣中,奕?是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与郭嵩焘关系很好,他是看过《使西纪程》并同意由同文馆刻印的,与宝鋆、沈桂芬、董恂等人政见拾合, 相处融洽;几十年致力于洋务事业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虽不在总理衙门,但在清朝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使西纪程》在刻印之前先曾由总署寄给他阅看过,是非常 欣赏的。因此,这些人对毁版《使西纪程》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样,围绕《使西纪程》一书的争执,两派意见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官司最后打到了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老佛爷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太后在郭嵩焘出使前觐见时,曾 当面向他保证:“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说闲话。横直皇上总是知道你的心 事。”[22]但此一时彼一时也,面对朝野上下、京城内外的一片谩骂讨伐声,此时的西太后当然照顾舆情要紧,顾不得什么事理了。于是老佛爷顺水推舟,于何 金寿参折上奏之日,即对总理衙门发下谕旨:“‘本日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请毁《使西纪程》一书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该衙门知道。’钦此。‘相应钞录原奏, 传知贵衙门钦遵办理可也。’钦此。”[23]于是,《使西纪程》毁版便成了不可上诉的终审判决。
三、导致《使西纪程》毁版的原因
郭嵩焘向总署呈送出使日记,不过是按照朝廷的要求来做的,“以期有益于国”;其出版也是赏识其书的主政者所为,郭嵩焘不能也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出版只三个 月时间即遭毁板,表面上看来是因为郭嵩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即何金寿所疏称的“有谋国者所宜言,而断非使臣宜言者”。但细究起来,则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人们头脑中传统的华夷观在作祟。千百年来,“华夷之别”、“夷夏之辨”成为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第一理念。在传统社会封闭状态下生长起来的士大夫阶 层,思想上一直自认为中国乃世界文明中心,一切华夏族以外的民族都是野蛮的“夷狄”,“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也。”[24]这种自大的观念, “蒙蔽了中国人的双眼,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认识,淡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而成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最大羁绊与障碍”[25]。古老中国的 大门,虽在鸦片战争中已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30多年,“用夷变夏”取代“用夏变夷”成为了新的时代发展要求,清朝当局中的一些远见之士也开始了“师夷 长技”的自强运动,但其认识程度也只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已,朝臣和士大夫之中仍普遍地充斥着一种虚骄自大之气。早在咸丰年间,大学士陈孚恩即 曾“力属”郭嵩焘“勿具折言事,盖恐误触忌讳”[26];出使之前的光绪二年二月初一日(1876年2月25日),郭嵩焘也曾谈到京城士大夫们“但以诟毁 洋人为快”,“所求知者,诟毁洋人之词,非求知洋情者也。”[27]出使之后,还曾愤愤不平地写道:中国“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 公议。”[28]在当时主张学习西方的士大夫中,郭嵩焘是较少背负沉重历史传统包袱的一位,他在日记中所论及的正是为世人所忌讳的“西洋事宜”,而且“一 再称扬”;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但以诟毁洋人为快”的朝臣和士大夫,而且是严厉的质问:“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所强调的正是“西洋立国, 自有本末”,其本在“政教修明”,且优于中国,这岂不是动摇“国体”?明明是夷狄,却说他们“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其构兵 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持重而后发”,这不是“媚外”和“有二心”又是什么?郭嵩焘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制器一类枝枝节节的问题,而是希望学习西方的一切长 处,直至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制度。这自然触及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内心深处固执的自大观念,搅动了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思维定势,能不激起朝野的愤怒 吗?《使西纪程》遭到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攻击,不过是盘桓在许许许多士大夫头脑中的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观念幽灵的再次发作。这是导致其毁板的根本原因所 在。
其次,是晚清政坛两大政治派系长期斗争的结果。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之后,清朝统治者无论洋务派还是顽固派都呼吁“自强”,但在如何自强的问题 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可称之为“借法自强”;顽固派则坚信自强之道就在于恪守祖宗之成法,可称之为“守法自强”。作为 朝廷实际的最高主政者慈禧太后,既重用顽固派,又利用洋务派,使之互相牵制。奕?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展的洋务自强运动,时时受到严厉的攻击也就可以理 解了。总理衙门虽设,但却被称为“鬼使”[29]之地,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极不光彩的衙门。而京师同文馆,则差点在顽固派的攻击下夭折。在这场较量 中,倭仁从此一蹶不振,顽固派也一时噤声不语,洋务派取得了胜利,但却不能改变“世道人心”。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的事件发生后,奕?等提出了六条“图 强”的总方针,大理寺少卿王家璧、通政使于凌辰等坚决反对,大骂支持奕?的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30],“如此谋国,诚不知其是何居 心”[31]。对洋务派一切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进步措施和言论,因循守旧的顽固派们几乎不放弃任何一次反对的机会,《使西纪程》中所表达的观点,给了他们 又一次这样的机会。如果说清流党对李鸿章等人的攻击主要限于暗流蜚语,对郭嵩焘则可以放手打击。通过对《使西纪程》的讨伐来打击郭嵩焘,进而打击洋务派, 是同光清流党下的一着妙棋。这一次攻击者针对的是一本小册子,是由总理衙门批准出版的,不同于过去所攻击的对象如总理衙门和同文馆等是经过皇帝谕准了的, 因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胜利。
第三,是清流党落井下石的结果。郭嵩出使之前既已遭到群情攻击。友人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惋惜,王闿运说他“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 [32],李慈铭说“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为之叹息也”[33]。有人编出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 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34]家乡湖南听说郭嵩焘竟要出使外国,俱怒不可遏,他们组织聚会,痛诋郭嵩焘,并结队 前往长沙玉泉山,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一门为此受惊不小。在福建被召时,郭嵩焘又因对云南巡抚岑毓英在处理马嘉理案中的种种不当具折进行参劾, 要求严办岑毓英,“以服洋人之心”,“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洋情以贻误国家者戒”[35],“以此大为清议所贱,入都以后,众诟益丛,下流所 归,几不忍闻”[36],一时“汉奸”、“贰臣”等骂名接踵而至。郭嵩焘当时所面对的舆论,正如他给两江总督沈葆桢信中所言:“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 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37]未出国门,郭氏就已落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不仅如此,景廉还曾上密折,要求“另简熟悉洋务大员出使外国,勿 令郭嵩焘前往”。[38]朝廷之所以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实在是因为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担此艰巨。因为出使外国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极为羞耻的差事,何况是“谢 罪”出使,谁愿意冒此风险呢?虽然反对郭嵩焘出使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是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郭氏在英国的一言一行,据说副使刘锡鸿每天都有日记,并向京师 的李鸿藻等报告。当《使西纪程》传到国内并出版后,李鸿藻等人看到郭嵩焘在书中大肆宣讲西方比中国强,再次触动了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祖训的 敏感神经,终于又抓到了攻击的口实。清流党落井下石的攻击,无疑是《使西纪程》毁板的最直接的原因。
四、毁板《使西纪程》是愚蠢之举
《使西纪程》在群情汹汹之中,经一道按何金寿所请“钦遵办理可也”的谕旨而惨遭毁板了,但这是一次没有赢家的愚蠢之举。
于郭嵩焘而言,所受的打击是多重的,也是终身的。其一,使他刚到英国不久便萌生退志,最后和刘锡鸿一起被撤回国,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 贴,指责他“勾通洋人”,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其二,“不独区区一身愿力无所施用,乃使仰天唏嘘,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縻,才智聪明亦为之遏 塞。”[39]其三,郭嵩焘死后,李鸿章为其立传赐谥的请求也因为“所著书籍颇滋物议”[40]而被否决。郭嵩焘所受到的多重打击,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更 是对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先进士大夫的一次无情蹂躏。
于郭嵩焘、刘锡鸿而言,则成了两人关系极度恶化的催化剂。在早期交往中,郭、刘其实是很好的朋友,郭嵩焘甚至曾把刘锡鸿当作自己的心腹;刘锡鸿出使,则还 是郭嵩焘本人和总署大臣毛昶熙等人的推荐;出使英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两人虽曾发生过一些矛盾,但至少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在对待学习西方问题上, 刘锡鸿也不像何金寿们那样保守顽固,郭嵩焘对他的评价是“于洋务颇有见地”,“所见原自高人一等”,只是“于世事多未谙悉”[41]。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两人关系开始紧张,但还至彼此撕破脸面。而导致刘锡鸿敢于“大怒诟骂,拍案狂叫而去”,实因其已得知郭嵩焘被何金焘所参,“惟此京师所同目指目为汉奸之 人,我必不能容!”[42]很显然,是《使西纪程》被攻击毁板,使刘锡鸿捕捉到了朝廷的政治风向,“迅速脱去热衷与精通洋务的外衣,以卫道士的面目出现, 夹杂私怨,无中生有,以此企图摆脱与郭嵩焘多年的干系,另寻靠山。”[43]
于清朝当局而言,《使西纪程》板虽毁而其书仍可读,实在没有太多的作用。因为毁板后却无法禁止人们抄阅,更何况上海《万国公报》还在连载。正如张佩纶所 言:“朝廷禁其书,而新闻纸接续刊刻,中外传播如故也”[44]。以现代传播媒介的传播特点而言,自然无法禁止民间阅读。朝廷官员和士大夫们如果愿意,也 只能听任其阅读。如前所述,在《使西纪程》毁板之后,王闿运、李慈铭等都还在阅读该书;曾纪泽也在看,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初一日,晴,卯正三刻 起,看郭筠仙丈所作《使西纪程》……饭后看《使西纪程》……”[45];前文所述薛福成之叹,想必他也是在看的。
于西学东渐而言,无异于遭到了一次恶性“病毒”攻击。郭嵩焘再也不愿将使西观感公开发表,“得何金寿一参,一切蠲弃,不复编录”[46],使广大中国士民 无法及时通过郭嵩焘的介绍来了解西方的先进文明;若皆引为鉴戒,“人人怕谈、厌谈”洋务,“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47]不能不影响到清政府 “自强”的努力。